
梁鸿近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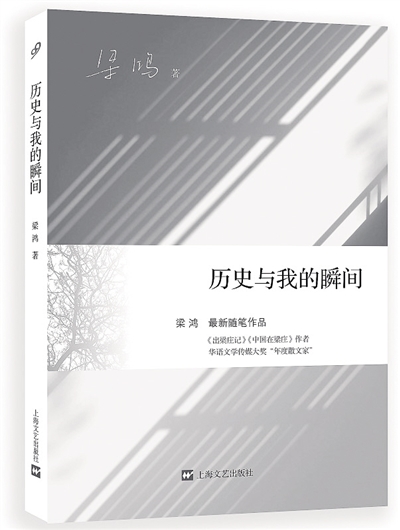
《历史与我的瞬间》封面
文\本刊特约撰稿 何晶《出梁庄记》《中国在梁庄》作者、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散文家”梁鸿最新随笔集《历史与我的瞬间》,日前由上海九久读书人与上海文艺出版社策划出版。梁鸿现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该书收录梁鸿27篇随笔散文,均为首次结集,沉潜的思索悲悯大地,优美的文笔直见性灵,是梁鸿继《出梁庄记》后带给读者的又一份礼物和欣喜。
该书分“归来与离去”“文学在树上的自由”“我们曾历经的沧桑”三辑。在梁庄和都市之间,归来、离去、重返;在书斋和乡野间,游走求索;读书论世,与大师也与自己相遇。
梁鸿说,重返梁庄最初或许只是无意识的冲动,但当她站在梁庄大地上时,似乎找到了通往历史的联节点。“从梁庄出发,从个人经验出发,历史找到了可依托的地方,或者,反过来说,个人经验找到了在整个时间、空间中阐释的可能。两者相互照耀,彼此都获得光亮。”
重返梁庄的意义
《中国在梁庄》和《出梁庄记》让梁鸿声名大噪,也让梁庄走进了许多读者的视野。但这两本书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社会学或人类学著作,梁鸿以亲属的身份进入梁庄,“这是我个人的梁庄,而不是社会学意义上的梁庄”。她回忆起当初自己重返老家并起念写书,似乎是完全无意识的行为,但今天回头看,她认为自己是在借梁庄来扩张个人经验,同时在历史的废墟上重建自己,“历史是活生生的‘在’,只有思考、反思,才能达到真正的存在。”
梁鸿认为,可以这么说,当“60后”知识分子在如醉如痴地吸收学习西方思想并借以批判中国政治与社会现实时,还只是少年的“70后”则如醉如痴地阅读来自于港台的琼瑶、三毛、金庸,并沉湎于一种自我营造的感伤和对传奇的向往之中,或因模仿港台剧中的英雄人物而成为小镇的不良少年,或如我这样,被像拔刺一样把叛逆的因子一点点拔掉。
梁鸿说,对于“历史”、“社会”这两大名词,“70后”是通过学习而得来的,是书本上的知识和家人的闲谈,哪怕并不遥远的“大跃进”“文革”,也只存在于支离破碎的话语之中,与现实的生活与情感都无关。没有上战场(虽然这战场只有在叙事时才有意义),没有经历宏大场景,没有荣耀、炫耀和言说的资本,没有被安排继承历史遗产,也没有来得及领悟新的历史规则并投入其中,却总是被历史的碎屑、生活的边角料所击中,这些碎屑是如此琐细、不重要,以至于根本不值得被提起,但却仍然实实在在地影响着一代人的人生。进入大学教书后,这种感受日益强烈。
历史就是你自己
1986年,几个来自南方的贩子来到梁庄吴镇,吆喝着收麦冬,一斤麦冬两块多钱。那一年,种麦冬的人家都“发财”了。富裕的“南方”第一次进入梁庄。当年,梁鸿的父亲把小麦地、玉米地全毁了,也种了五六亩麦冬,收获时,雇了二十多个人,父亲每天计算着能挣多少钱,还多少债,剩多少钱,家里村里,到处是欢声笑语。
但是,第二年,南方的小贩没有出现,吴镇的许多人家因麦冬而破产,抵押房产、跑路、逃避债务,有熟识的人家一再筹措路费到广州去要债,但每次都凄惨而归。在梁鸿的记忆里,这是“南方”作为具象第一次来到北方的乡村里。南方与北方、城市与乡村,彼此间的二元对立和残酷性就这样出现在日常生活中。
1988年,15岁的梁鸿在县里念师范学校。一天,她和女同学在走廊聊天,被发现批评时,嘟囔了一句:“又不是在搞同性恋。”当天晚自习,班主任把梁鸿叫出了教室,愤怒地说:“你知道那是啥吗?你还要不要脸?”
围绕这件事,梁鸿被连续批评了六天,“我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同性恋’是一个来自于资产阶级社会的、不道德的、罪大恶极的词语。”梁鸿说,在这背后,有一个洪水猛兽般的“西方”:色情的、无耻的、变态的世界。“西方”就这样以一种奇异的纠缠状态出现在1980年代后人中国日常生活中。梁鸿用这两个事例来讲述她如何用个人经验找到进入历史的切入点。“我发现,当把目光有意识地投向与‘我’相关的事物,你会很容易察觉到它内在的生长性和历史性。”她说,回到梁庄于她而言是一种激活,她重新找到了思考的起点和支点,并激活了自己的生活——学术生活和实在生活。
在梁鸿看来,历史意识的生成与其所处的历史阶段无关,重要的是“我”与历史的联结方式。历史就是你自己。她说:“能粉碎大历史框架的恰恰是个人记忆,是历史空白处的碎屑和不引人注意但却又久远的伤痛,它影响甚至制约着历史的运行。”
最后,梁鸿说,历史赋予了我们一个个瞬间,能够对这瞬间所包含的形式及与世界产生的关联进行思考,我们就汇入了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洪流。
(本版图片由本报资料库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