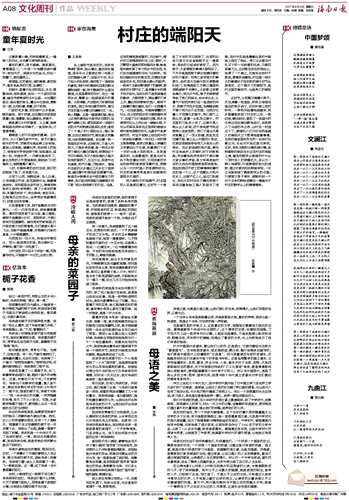岛上端阳节前后的天,突然变得高旷起来,抬头看去,越往深处越蓝,连朵朵白云都被这种一年里少见的蓝融化掉了,但每天午后,乌云不知从何处赶来,准时落下一场短促的豪雨,把村中的椰树和四周的野生植物浇洒一番,树木碧绿的叶丛更加碧绿,尤其是椰树的羽叶,在过一遍雨水后,飘散出一股盛装其外的喜意。大雨停歇,天空很快又恢复雨前的蓝色,透过鸟鸣如歌的树林,看见天空的蓝光与薄云的缥缈交汇一处,映入眼瞳。这是一幅蓝调的画,海岛上这样的景色似乎是司空见惯的,但静气凝眸之后,便发现其实一年里村庄的天气和物候总是面孔多变,像极了一个高人的心眼和念头,难以琢磨,比如这端阳时节,哪怕是大雨瓢泼,也依然溽热难捱。依仗着一阵一阵西风的吹来,这样的热,不是七月流火,不是秋旱烘燎,是一种在太阳底下煨在火塘边的感觉,联想到这个节日叫端阳,终于大抵知道古人感天知地的聪明了,五五为正,阳居中位而高悬,热气升腾,万物俯伏。难怪村庄前的大水塘这几天水位下落明显,躺在塘中的黑色淤泥冒着气泡,鲶鱼在半缺氧状态中扭动着无力的滑脊,鸟们站在树荫里只是瞎聊天而不敢飞向太阳伺候下的天空。但是,这样的痛苦是短暂的,日过晌午,潜伏的云层翔游到村庄上空,顿时,千万颗硕大晶亮的雨粒砸向水塘,鲶鱼很快就恢复了体力和水中的生活,鸟们抖抖湿漉漉的羽毛飞出树林。雨粒也砸向村庄的黑瓦顶,反弹成无数绽放的水花,同时奏出爵士的鼓声。一些来不及躲到野菠萝下的鹅群,被突来的大雨吓住了,直伸着长长的脖子向天仰叫,但仰叫的不是那首著名的鹅诗。大榕树底下,围坐着的不穿上衣、露出深深锁骨的老人,榕树干上挂着的调皮童孩,他们一边骂着天气,一边往家里跑。村路旁裸露的大石头,在太阳和雨水的交替物理作用下,加速了它们崩裂的过程,雨水在滚烫的石头上汽化成一缕缕白烟,大石头的面目其实在这场雨的缕缕白烟中就有细微的变化,沧桑的气息新鲜历历。村庄外坡野上站在雨中的一块块经年墓碑,一年旧过一年的碑文渐渐模糊,致使记录墓主人荣耀的文字最终归于无痕,向墓碑们下这一手的也是太阳和雨水。自然是温和的,也是霸道的,更是无时无处不制定着法则的,它用戏虐的手法和独特的修辞改写着村庄、坡野以及一代代村里人的容颜和时光,村庄的故事常常是被太阳晒黄和被雨水打湿的。
因为端阳天的怪脾气,村庄里的人总是顺应着它,这时节一个斑驳了千年的节日赶来了,古老的内容只是它无法省略粽子这一道美食,其他的已经说变就变了。因为粽子,大家要做的事情大致相似了,不外乎就是把粽子绑出饱满好看和好吃不腻来。而秀仁家有更大的事要办,他的老大在端午那天要娶媳妇进门,他得提前几天绑三筐猪肉咸鸭蛋粽子送聘礼,大家都过来帮他操办,因为天气热,粽子的保鲜便考验了秀仁的脑瓜,他半夜出去,从暑气不到的井底打回一担透凉的井水,把粽子沉在水缸里,拍胸脯说粽子浸个两天也不会发馊。也因为忙着儿子送聘礼的粽子,秀仁顾不上剃头发,留着一头乱发过端午。村庄里的习俗多少年了,过端午男人剃头女人绞面,好干净地度节和迎接神公进家受祭。秀仁于是白天黑夜就戴上了一顶太阳帽,把乱发压在帽子里,晚上出入村里的小卖店,还被店老板娘夸他有几分赵本山的神采。在这段连绵的热天里,绑在村庄电线杆上的喇叭时不时就响起,夹杂着电流声传来村干部纠集大家议事的声音,县文体局派给村庄的大戏台和篮排球场即将落地,选址和选日子动工的事情牵动着村庄的每一个人,这个话题比大热天还炙人,比粽子还上心,经过几轮商议,年纪大的村伯终于蹲在树荫下面色庄重地给工程人员指点了迷津,在村中孔庙连着嗮谷场的中轴线上选定了地址。秀仁过去跟生产队买下的一间坍塌的社房,只剩四面墙兀立,正好就在戏台的选址上,他想了一个晚上,天亮后去找村干部说,愿意拆房腾地,村庄里一桩天大的事情终于在炽热的端午时节尘埃落定。这个普天下的端阳节,是村庄里的端阳节,也是秀仁的端阳节。
这时节,太阳整日端着个架子,天空虎着一张蓝脸,积雨云徘徊在遥远的地平线下,时刻听候上苍的吩咐。一阵热风贴着地面趟来,雨水跟着就来到了村庄的上空,一阵狂泄,瞬间刹住,像极了一场盛大的交响正在如痴如醉地进行,突然拐入了乐曲的休止符,让村庄一时适应不了,疲倦的人们只好在热浪袭人的端阳天之下敬畏地做着事情,自然的暗室里所发生的一切他们无需过问,无论对天地还是对神祇。这时,有机生物的分解和被分解、各种植物的疯狂生长正在村庄的地里上演,墙角的野芋头肥阔的叶片比一顶村庄人的草帽还大,足以为一群小鸡遮雨,叶绿素借助阳光的透射,通过叶筋向四处野蛮伸延,一天之间就染绿了整株野芋头的衣裳。只要俯下身子谛听,便能听到一个关于生命的野性话题在一棵幽长于村庄的野芋头上的肆意喧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