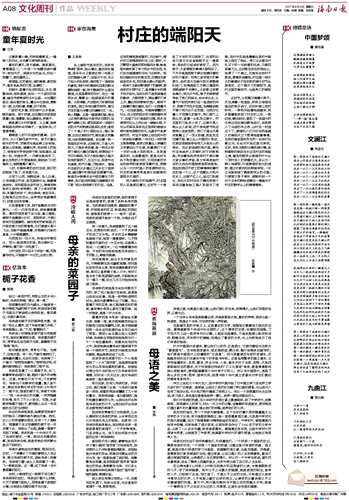母亲住在家里的时候,她的菜园子总是绿莹莹的,挤满了各种各样的蔬菜。生机勃勃的油麦菜、圆鼓鼓的椰子菜、纤细苗条的豇豆、粉里透红的西红柿、羞答答的胡萝卜……每次一回家,母亲的菜园子就变一个样,仿佛永远不会疲倦。
有一年春天,母亲随意种了五六畦玉米,没想到长势良好,一下子把菜园子变成了玉米地。长长的玉米穗静静地垂挂下来,宛若一幕幕垂帘。儿子特别喜欢外婆的这一片玉米地,总爱窜入其间,一边摘玉米,一边与蝴蝶嬉戏流连。午后的阳光轻轻地落在母亲和儿子的脸上,静谧而温暖。
有时是青菜,抽出长长的黄色的花,引得蝴蝶在其间翩跹起舞;有时是红彤彤的圣女果,陪母亲摘菜摘累的时候,就可以直接摘下放入口中;有时又是生命力极其顽强的韭菜,齐刷刷地切下一捆又一捆,没过几天又开始油油地绿了起来。
母亲种的菜她是无论如何都吃不完的,除了送人就是打包给我,或者是让我回去采摘。那是一段特别透明的时光,连阳光都薄得长出了羽翼。怎么都摘不完的豆角,给文昌鸡做佐料的香菜,拿来清炒却怎么都吃不腻的蒜。回一次娘家,就是一次大丰收。
最喜欢的是与母亲一起给丝瓜搭瓜架,每搭一根,就仿佛能感觉到丝瓜的触角已轻轻地攀爬上来,就仿佛能看到那一朵朵迎风招展的丝瓜花已绽开了笑脸。等到小丝瓜真正结上瓜架的时候,母亲就会用报纸轻轻地把它们一个一个地包裹起来。我喜欢站在时光之外,细细地端详着母亲打理菜园子的每一个细枝末节,柔和的光线落在母亲的额角,青丝渐渐变成了白发。
后来母亲在菜园子的一个小角落里种了一小片“指甲草”,她是想把逐渐变白的头发染成植物的颜色。我曾经幻想过在午后的阳光下为母亲染发的情景,可时间一天天过去,我对母亲的承诺却一直未曾实现。
那日回家,没有父母亲的家。所到之处,竟已落满了尘埃。父母亲只是离家一两年,短暂的荒凉却覆盖了几十年的繁华。那种荒凉感一直如影随形,强烈地撞击着我的心灵,让我如此怀念那些母亲在家的日子,让我如此怀念母亲还未曾荒芜的菜园子。
我突然变得害怕又无助起来,从未认真倾听过母亲的声音,从未审视过自己对母亲无休止的获取。如果有一天母亲突然抽身离去,宛如那多年来一直郁郁葱葱的菜园子,一下子变得荒芜,乃至杂草丛生。我又该如何面对生命里的这样一种残缺呢?
直到那天在小姨家,静静地坐在天井下看小姨用“指甲草”为母亲染发,我空洞的心才开始慢慢温润起来。我轻轻拨开母亲的发丝,那掺杂在青丝间的点点白发,每一根都刺痛了我的眼。我默默地注视着,直至那些被“指甲草”温柔染过的发丝,渐渐散发光泽。它们多么像母亲那年种在菜园子里的“指甲草”,随风摇曳,婀娜多姿。
我从来没有想过有那么一天,在微风的吹拂下,母亲也会老,也会像她的菜园子一样,渐渐荒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