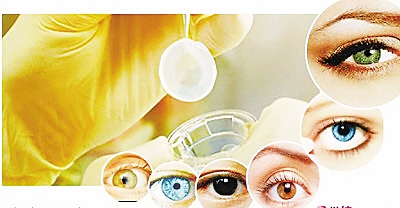现状
许多人排队等待器官救命
我国是世界第二器官移植大国,但公民自愿捐献器官率较低。2015年起,我国全面禁用死囚器官。北京、江苏、湖北、上海等地从事器官移植的医学专家认为,器官来源原本就很紧张,现在就更加紧张了。
然而,等待器官救命的患者的痛苦、绝望又让人刻骨铭心。记者在北京、上海、江苏、湖北等地大医院采访了解到,凡是有资格做器官移植手术的医院,几乎都有人在排队等待器官救命。遗憾的是,有部分患者在等待中离开了这个世界。
“我们病房内几十个病人仍在苦苦等待合适肺源。”中华器官移植学会委员、无锡市肺移植中心主任陈静瑜去年底发的这条微博引起广泛关注。
国内较早开展肺移植的中日友好医院,“已经4年没做过肺移植手术了,就是找不到供体”。中日友好医院大外科及胸外科主任刘德若说。
作为器官移植的专家,刘德若、陈静瑜等太了解器官稀缺带给病人的痛苦了。“由于供体太少,一个受体从决定可以接受肺移植开始,通常需要等待1.5至3年时间才能如愿,很多患者就在等待中死亡。”陈静瑜说。
原因
捐献者义举得不到应有肯定
我国器官捐献事业,除了规范禁用死囚器官外,依然有很长的路要走。
当前较流行的说法是:我国每年大约有150万器官衰竭患者,有30万适合器官移植方式治疗,每年仅有1万多人能得到器官移植的救治。
中国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主任委员黄洁夫对此有不同看法:“无法进行移植不都是因为缺少供体,有很大一部分病人因经济原因放弃手术。还有一个现实原因是,我国能做器官移植手术的医生只有几百人,具有器官移植资质的医院只有169家。”
不过,记者在医疗机构采访时,众多从事器官移植的医务人员认为,在医患矛盾突出、官办慈善机构又陷入信任泥沼的当下,器官捐献事业发展举步维艰。在“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的传统观念影响下,捐献者义举得不到应有肯定。
中国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2012年在武汉和广州进行民意调查,40%以上的人表示不确定是否会捐器官。“他们不知道这个器官捐献是不是公平公正的。”黄洁夫说,这可能是原因之一。
黄洁夫说,我国自开始自愿捐献器官以来,至今年1月31日,全国实现公民逝世后捐献案例3326例,仅2014年实现近1700例,超过之前历年总和。“这表明器官移植依赖死囚的局面已经打破。”
“器官捐献率低,落后的不是传统观念,是行政管理的体制,把管理体制搞好,公民捐献意愿就会提高。”黄洁夫说,“公开、透明、可溯源的器官分配体系至关重要。”
当前,我国研发并启用了人体器官分配与共享计算机系统,以患者病情紧急度和供受者匹配程度等国际公认的客观医学指标对患者进行排序,用技术手段最大限度排除和监控人为干预。公众的期待是,让这些措施能够实实在在地执行下去。
担心
如何认定患者死亡
如何认定患者死亡,是影响器官捐献的关键问题之一。患者依然担心,“会不会我签署了捐献器官的协议后,医院就不会积极救治我了。”
黄洁夫说,结合我国传统文化,我国器官捐献工作以心死亡为法律依据,制定了中国器官捐献死亡判断3类标准:脑死亡;心死亡;心脑双死亡。此标准由神经科与重症监护医生等经过严格训练后判定。
从事器官移植的医疗界专家指出,“心死亡”“脑死亡”和“心脑双死亡”三者并存,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由于三者之间的界限比较模糊,很容易产生法律纠纷。
参与过多次器官移植手术的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普外科一位专家表示,假如死者家属质疑医生因摘取器官而抢救不力,医生将百口莫辩。
多位器官移植专家共同建议,国家层面虽然出台了死亡认定技术规范,但希望建立严格的第三方评估机制,从制度上明确捐献者、医务人员和受捐者各自的责任和义务,以避免不必要的纠纷。
问题
制度设计面临的问题
现在全国在册的器官捐献协调员仅547位,其中169位是红十字会专职协调员,其余为器官获取组织专业协调员。“相比于我国的器官捐献发展趋势和需求,这个数量远远不够。”中国人体器官捐献中心业务部副部长高新谱说,在禁用死囚器官,完全依靠公民自愿捐献器官的当下,这一问题显得更为突出。
目前我国对捐献者的身后事没有配套优惠措施。记者采访时,有人表示,一个人捐献了自己的器官,救了另外一条甚至数条生命,在他的身后事上,比如火化、殡葬费等方面却得不到任何抚恤,会令捐献者寒心。
再就是医疗费用问题。2014年,中国人体器官捐献中心处理的捐献案例1699个,挽救了3400多人。“这些捐献者往往面临大量的医疗债务,1200多人需要这方面的救助。去年国家大约拨付了84万元,远远不够。”高新谱说。
针对上述问题,高新谱说,我国正在对660名协调员进行培训,通过了资格认定考试,即将上岗。
黄洁夫等专家特别指出,对捐献者身后的困难家庭给予救助,绝不等于器官“买卖”或“交易”。要明确捐献者家庭申请救助的程序,掌握适宜的救助标准,既要确保捐献人和法定受益人的基本权益,又不能让器官捐献“自愿无偿”的原则被扭曲。
一些器官捐献者的家属表示,希望对人体器官捐献者困难家庭,进行人道抚恤或困难救助,并协同为捐献者家属提供缅怀亲人的场所,建立纪念墓地、纪念林、纪念碑或纪念网站,缅怀和纪念器官捐献者。
记者 李亚红 顾瑞珍 廖君
(据新华社电)
我国百万人口年捐献率5年增长60倍
但比例仍偏低
近5年来,我国百万人口年捐献人体器官率增长了60倍,年均器官移植数量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进展迅速,但从数据看,比例仍然偏低。
(据新华社电)
感恩回报,让等待之路不再漫长
——来自器官移植患者的呼唤
2015年1月底,等待6年之后,26岁的湖南女孩李丽(化名)终于移植了来自姚贝娜的部分角膜,可以再次看清这个世界。而此前,因为患有先天性角膜皮样瘤影响了视力和外观。
相比李丽,30多岁的湖北农民工小邓却没有这么幸运。小邓的左眼被啤酒瓶碎屑划伤,苦等一年多也没有等到合适的角膜。
湖北、上海、辽宁等地多位接受或等待器官移植的患者告诉记者,等待生命礼物道路实在太漫长,希望也很渺茫,如果他们有机会等到被捐献的器官,他们也一定会以同样的举动回报社会。
袁守汉:“我还这么年轻,要让人生有价值”
去年8月,38岁的湖北人袁守汉被确诊为脑肿瘤,在武汉做完手术后3个月就复发,并导致双目几乎失明。今年1月初,他来到上海希望能够为自己寻求一线生机,但因为手术难度太大,医生迟迟没有通知他准备手术的时间。
在等待手术前,袁守汉就表达了器官捐献的意愿。他告诉记者,以前死守着传统观念,认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无论生还是死,都要完整。“现在想想我还这么年轻,除了脑子,其他地方都好好的,白白浪费太可惜了。”袁守汉说。
1月中旬,医院采取全新手术方式,不开颅从袁守汉的鼻子里进去微创切除了肿瘤和瘢痕。手术成功后,为了表明自己的决心,袁守汉正式签署了一份器官捐献的志愿书,承诺无论自己以后遇到何种情况导致生命无法延续,都会无偿捐献自己的器官。
小孟:因为感恩才要回报
14岁那年,老家在辽宁的小孟右眼受了外伤,因为当时视力没有受到影响,小孟一直没有去医院就诊。
去年10月,眼看着右眼视力越来越差,小孟拿着打工的全部积蓄来到辽宁沈阳市何氏眼科看病,医生诊断需要移植眼角膜。
小孟说,自己还算比较幸运的,只等了三个多月,就等到了可供移植的角膜。“但这三个多月里的每天都很煎熬,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得到角膜?不知道拖的时间一长,会不会加重病情?”眼睛还蒙着纱布的小孟告诉记者,自己每隔一两天就要打电话到医院去问一下。
如今,做完眼角膜移植手术的小孟右眼视力逐渐恢复,他说,虽然不知道捐献给自己角膜的是谁?自己也没有办法向他的家人表示感谢,但他决定等出院后就去签下角膜捐献志愿书,希望以后能够帮助到其他人。(据新华社电)
辽宁“劝捐第一人”
杨东文11年 带动2000余志愿者
初中学历,职业是一名保安,在器官捐献这个对很多人而言稍显陌生甚至有所抵触的领域,45岁的杨东文已经坚守了11年。
与红十字会结缘始于2001年,辽宁红十字会号召市民加入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杨东文所在的中老年自行车队就申报成立了“红十字会自行车宣传队”,在骑行健身的同时,宣传捐髓救人知识。2004年,了解到器官捐献缺口,杨东文发起成立了辽宁省自愿捐献遗体器官志愿者俱乐部,成为国内最早宣传捐遗的志愿者俱乐部。
工作初期,他数不清面临过多少冷嘲热讽、白眼甚至辱骂,有在病床前家属坚决反对,最终反悔的;有根据捐献者电话上门登记却吃到闭门羹的;还有人在QQ、微博上进行辱骂……但杨东文从未放弃,他坚信自己工作的意义。为了不错失任何一个电话,他24小时开机;在家里、单位和红十字会,他准备了3个背包,里面有各种材料、表格,以便接到捐献者电话可以随时出发……
志愿服务10年,杨东文坦言最对不起家人。他节假日大多在外面做宣传,一年陪妻子逛不上一回街。他收入微薄,却为志愿服务前后花费3万余元,一家三口至今还住在房龄30多年的不到40平方米的房子里。
在杨东文和省红十字会的共同努力下,目前辽宁报名参加人体器官捐献的志愿者人数已经超过2000人,实现捐献遗体300多人,有60多人因角膜移植手术而重获光明,40余人因器官移植获得新生。
让杨东文欣慰的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眼角膜捐献、器官捐献。“当代雷锋”郭明义及多名辽宁省、市道德模范也加入志愿者队伍,以他们的感召力影响着更多人。记者王莹(据新华社电)
2000万人口小国成为“世界之眼”
——探秘斯里兰卡的眼角膜捐献
印度洋上,一个仅有2000万人口的国度竟然是全世界最大的眼角膜捐赠国——从上世纪60年代至今,斯里兰卡国际眼库已捐出67000多枚角膜,涉及57个国家、140多个城市。
“最多的时候一天接到过50枚眼角膜”
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7区,耸立着一座金色人像——这是著名的斯里兰卡眼角膜之父哈德逊·席尔瓦博士。塑像身后,便是驰名世界的斯里兰卡国际眼库大楼。
“按照计划,明天夜间航班会有20枚眼角膜空运到中国厦门眼科中心,现在我们有了8枚,预计今晚到明天早上会陆续收到十多枚,”在位于眼库大楼三层一侧的实验室内,贾纳特指着处理完毕冷藏封存的8枚眼角膜说,储存眼角膜的冰箱一侧挂着一面小小的锦旗,表明冰箱是由中国成都爱迪眼科所赠。
20枚,仅仅是一个保守估算后得出的数字,贾纳特非常轻松地表示,根据经验,角膜来源和数量无需担心,“几乎每天都有新增的角膜送来,每天20枚是比较合理的数量,多了就不好处置。最多的时候一天接到过50枚眼角膜。”
“每一任总统都捐献了眼角膜”
但仅仅是在上世纪60年代,斯里兰卡的眼角膜捐献还处于空白,唯一的眼角膜来源是每年数例的死刑囚犯。
50多年前,身为医学博士的席尔瓦投身斯里兰卡眼角膜捐赠事业——在亲眼目睹收治的不少眼疾病人因缺少眼角膜而导致失明后,席尔瓦博士怀着沉痛的心情写下那篇著名的《人死眼犹生》(LIFE TO DEAD EYE),这篇文章被后人普遍视为点燃斯里兰卡眼角膜捐献热情的一簇火苗。
“斯里兰卡每一任总统都捐献了眼角膜。刚刚就职的新总统西里塞纳和夫人5年前签署了捐赠书,前总统拉贾帕克萨还担任部长时就和夫人决定捐赠了。”
捐赠网络由一个个骑在摩托车上的乡村医生构成
在贾纳特看来,除了宗教信仰这一先决要素无法复制外,在世界其他范围内推行角膜捐赠,应该做好“长期准备”,建立强大的采集网络系统,并且从制度上形成规范。
在斯里兰卡6.5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分布着450多个联络处,几乎每个乡村医生都在国际眼库得到过专业培训,确保在逝者去世后珍贵的4个小时内完成意愿询问、捐赠签署、球体摘取并第一时间送达眼库。
为保证角膜捐赠效率,每一个联络处的医生都有一辆坐骑——斯里兰卡庞大的角膜捐赠网络,正是由一个又一个骑在摩托车上的乡村医生构成。
记者 杨梅菊(据新华社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