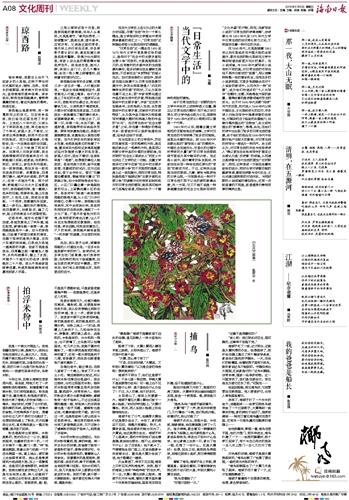在当代文学史上迄今为止的大部分时间里,尽管“生活”作为一个核心概念,是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中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日常生活”这种提法却很少出现在相关的语境里。
“日常生活”这一概念在1950至1970年代文学中更具普泛性的涵义,是相对于“社会中的主要矛盾和主要斗争”而言的,大致是指那些平凡的、没有激烈的矛盾冲突的生活场景和事件,很多时候也包含着缺乏典型性、不反映社会“本质特征”的涵义在内。如对茹志鹃的小说创作,批评家在指出她善于从日常生活场景的展开中,抉发出那些普通人“内在的精神世界的美”的同时,又认为其存在着不足之处,即“作家有责任通过作品反映生活中的矛盾,特别是当前现实中的主要矛盾”,作家“应当努力创造条件,主动地深入生活,去发掘现实中的主要矛盾,反映时代的本质特征”,认为其作品只能作为那些描写所谓重大题材和英雄人物的作品的“补充”。在日常生活与“社会主要矛盾”之间,存在着一种微妙的等级关系:前者或许可以曲折地通向后者,但将永远低于后者。
在马克思主义的文学观中,历史的发展有其一定的规律和方向,是否能反映出这一规律和方向,是其用以判断文学作品的价值的主要标准,在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定义中也突出了文学的这一功能。左翼文学批评对文学中反映“社会中的主要矛盾和主要斗争”的不厌其烦的强调,正是从这一面向展开,因而日常生活,特别是那些不能被这种“主要矛盾和主要斗争”的读解方式所有效识别和吸斥的日常生活的描写,就因其可能冲淡乃至淹没前者,而始终处于一个暧昧和危险的境地。
由于日常生活在这一时期的当代文学中所处的上述种种语义位置,真正以日常生活为题材(而不将之非日常化)的文学作品也极为少见,邵燕祥写于1960年代初的《小闹闹》可以算是一个代表。
1980年代以后,随着左翼文学规范的支配性地位的崩解,文学对日常生活的书写获得了较多的可能性,呈现出丰富的样态。到1980年代中后期出现的“新写实小说”的潮流中,中国社会在城市化、市场化的过程中所带来的大量“新”的日常生活琐碎细节更成为其中触目的内容。在这些小说中,面对庸常的俗世现实,作家往往采用一种将生活还原化的“客观”的叙述方式。不过,这种突出呈现生活的琐碎、凡庸、惰性与耗损性的文学企图,一方面提供出一种对于日常生活不同于以往的新的叙事态度,另一方面,它又不能不说是一种承继着此前的社会文化现实而来的“文化失望”的产物,因而,在新写实小说的“日常生活的诗情消解”、非诗意化与1950年代至1970年代文学中日常生活的非日常化努力之间,又明显存在着一种对位的关系。
在1990年代,尤其是随着1993年以后市场经济在中国大陆的全面展开,都市生活的物化现实在文学中得到较诸此前更为充分的展示。在小说领域,与1980年代新写实小说有所不同的是,对日常生活的书写往往不再作为叙述的“前景”,用以消解种种整一性的意识形态,在相当多的小说家那里,它更多地被融合在对个人经验的叙述中,从而作为一种“后景”,成为他们所追求的“个人化写作”在题材、主题、风格等各方面的参量。值得注意的是诗歌领域所发生的变化。出于对1980年代后期“纯诗”风气的反思,和对进入19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文化现实变化的应对,许多诗人开始在写作中强调诗歌的包容性,对复杂的当下经验的处理能力,如萧开愚所提出的“及物性”,孙文波所提出的“叙事性”,等等,由此,在他们的诗中也出现了较多的日常生活的场景,由于他们的观念在1990年代中后期开始产生较大的影响,对日常生活的抒写也一度成为一种风气。孙文波认为,对日常生活的关注与包容使诗人“得以更加自由地将写作扩展至过去被认为是‘反诗意’的领域,从而建立起诗歌与当代生活的更加广泛的联系”,因而,这种尝试一方面包含着实验性的成分,同时也有对诗歌功能的重新考虑,意图在诗歌与当代社会、文化间建立起积极的对话关系。与同时期的小说领域的情况相比,还有一点较显著的不同是,前者通常仍秉有浓厚的精英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