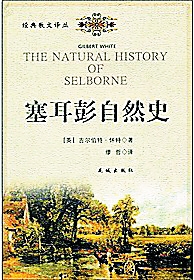《塞耳彭自然史》自初版220多年来,一直静默地在世界各地流传。最早介绍到我国的是周作人,该书的中文名“塞耳彭自然史”也是周作人取的,发表在1934年的《青年界》上,周作人还认为自己取的书名“一看有点生硬”,看得出他对此书非常感兴趣。现代作家李广田的散文集《画廊集》中也有一篇《怀特及其自然史》的赏评文字,“这不是科学家的自然史,而是一个自然的爱好者,用艺术的手笔,把造物的奇丽现象画了下来的一部著作。”周作人曾有把《塞耳彭自然史》译成中文的想法,但因别的事而放弃了。叶灵凤在《几本当译而未译的书》中说,怀特的这本书有草木虫鱼鸟兽名字的大障碍,该书的译者应当是“一位翻译好手和一位学贯中外的自然学家合作”,他自己没能译成。直到2003年国内才面世了由缪哲翻译的比较完整的中文译本,这本书广受称赞。
怀特对塞耳彭村生态环境的兴趣,一方面来源于其对自然的天生热爱,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工业革命前期某些与工业化潮流不相符合的观念。处于英国偏僻地区的塞耳彭村不同于伦敦、曼彻斯特等大工业城市,在它宁静、和缓的发展轨迹中,“那时候的时间,还不是金钱,而是享受、修养和自我发展的机会”。怀特作为牧师,“正是怀着尊严和不枉度生命的感觉”,对家乡塞耳彭村自然环境的细致考察,于展现自然美的同时孕育了更为深刻的生态伦理思想。在工业文明的触角尚未全面伸展开的塞耳彭乡村,人与自然的矛盾在颇为落后的生产方式下已经存在,而怀特已经敏锐地觉察到这一点。除了当地的传统生产方式对自然生态环境所导致的某些破坏之外,他在《塞耳彭自然史》中还叙述了另外一种危害,那就是人称“伦敦烟”的薄雾:“这雾作蓝色,略有煤烟的味道,常乘着东北风飘来我家乡,其源头应该是伦敦。这雾的气味很浓,据说可致虫害。雾过后常有干旱天。”在叙述岩燕的习性时,“岩燕子爱去城里,尤以近大湖或近河者为甚;即使空气的浊恶如伦敦,它们也喜欢……但落户于伦敦的岩燕子,羽毛上带有空气里的尘垢,这显然是环境脏所致。”
18世纪的伦敦,由于烧烟煤的缘故,空气质量很差。距离塞耳彭村40英里的伦敦,在18世纪中期就已经存在严重的空气污染问题,影响波及周边地区,连塞耳彭这样的偏僻
乡村亦未能幸免于难。怀特在书中的描述,准确地指出了污染的源头及其后果,对生态环境的渐趋恶化表现出深刻的忧虑之情。
怀特是博物学者,也是文学家。《塞耳彭自然史》首先是一本自然科学史,“在科学史中起着脚踏石的作用”,人们普遍将其视为达尔文、斯宾塞、赫胥黎等一代思想巨人的先驱。构成这本自然史的尺牍体散文优美清明、亲切生动,具有牧歌的情调和风度,李广田称它是“一部永世的乡土文学”,周作人称它是“十八世纪英国文学中一异彩”。《塞耳彭自然史》更多地具有了环境保护和生态意识的新意义,塞耳彭村亦被人们视为工业文明时代所向往与追求的精神家园。
在我们的阅读视野中,塞耳彭村构成了人类与自然相处的和谐天地。“往来于苏塞克斯的山岗上,考察这些雄伟的、蜿蜒而奔走的群山,却年年有新喜悦;每一次穿过它,都可见到新的美景……欧洲最好的风景亦不过如此。”这样一个自然、淳朴的塞耳彭或许正是人类历经种种现代文明的诱惑最终追求的归宿。然而,能否实现回归这一美丽的愿景恐怕还取决于人类自身的觉悟和努力,否则那将只能是一个永远虚无飘渺的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