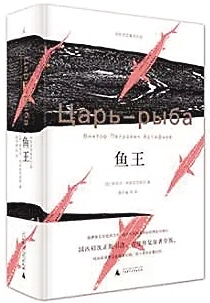经历过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读书热的人们大概还记得,1982年,《鱼王》汉译单行本首次在中国出版的时候,当时它掀起了怎样的一股如饥如渴的追捧热。这不仅是因为当时国内普遍存在对俄罗斯文学的喜爱之情,更是因为《鱼王》这本书本身作为文学作品的可读性价值所在。
今年五月,广西师大出版社重新再版《鱼王》,在国内引起巨大关注。有作家说,过了35年,维克托·阿斯塔菲耶夫又借着《鱼王》复活了。
他是西伯利亚之子
维克托·阿斯塔菲耶夫,当代著名抒情小说作家,出生于1924年,在十月革命的时代大背景下度过了童年和青少年时期。母亲早逝,先由祖母抚养,后来进入了孤儿院。
了解阿斯塔菲耶夫作品的人都知道,他的出生地对他日后成长为作家的重要影响:他在西伯利亚大草原上的一个小村庄里出生。西伯利亚谜一般的原始森林,奔突不息的叶尼塞河与静谧的冰雪冻土,给了他一颗感应自然音色和光谱的纤细之心。他曾与拉斯普京一道,被称为“最纯粹”的两个俄罗斯作家。在他的代表作《鱼王》和《树号》中,他一遍遍描绘着这片北极圈边缘地带的森林和叶尼塞河,以及在那里的外来者和原住民的生活足迹。
像那一代的所有作家一样,阿斯塔菲耶夫参加过卫国战争,并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发表作品,国内曾出过他的一部早期作品《牧童与牧女》,里面可以看见作者早年生活的痕迹。
阿斯塔菲耶夫不是天才性的人物,这位出生在西伯利亚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一个农民家庭的孤儿,品尝过流落街头的艰辛,在二战中受过重伤,退役后做过形形色色的底层工作,然而生活里的苦难并没有马上转化为文学上的才华与声名,1952年才出版的第一本小说集《明春之前》,那一年他二十八岁。1959年,他参加了高尔基文学院高级文学讲习班,笃定从此以文学为事业,他的小说开始定期“默默无闻”地在各种杂志上发表,直到1967年,才首次在前苏联文学杂志的No.1《新世界》发表作品,当时作者已经四十三岁了。1976年,年过半百的作家拿出了《鱼王》,这部长篇小说如今是俄罗斯文学当之无愧的经典。
“钓鱼人” 钓出了《鱼王》
阿斯塔菲耶夫从1951年开始发表作品。1959年,《老橡树》为作家带来了声誉。之后作家佳作连篇,1960年的《流星》写的是卫国战争期间一对男女的军医院相识并相爱,然而出于对生活的责任感未成眷属的故事。1966年的《偷窃》以孤儿院里两次互为因果的偷窃为线索,描写一群性格迥异的孤儿和在他们身上萌生的“俄罗斯的怜悯心”。《牧童和牧女》(1971)被作者称为“现代牧歌”,主人公负伤后,在对恋人的苦苦思念中死去,表现超越战争的残酷之上的人性的力量。由23个短篇和一部中篇组成的系列小说《最后的致敬》(1957—1977)贯串着作家对生活中稳定的道德价值的关注。作品在展示主人公维佳成长的同时,刻画了一系列普通的俄罗斯人形象,其中祖母象征着“人的不朽,人民的生命力和人民永恒的记忆”。之后便是这部给作家带来更广泛声誉的作品《鱼王》。
1976年,长篇小说《鱼王》首次在苏联出版。当时,来自西伯利亚的作家阿斯塔菲耶夫是俄国文坛最耀眼的“后起之秀”。他毕生都徘徊在家乡西伯利亚叶尼塞河流域,不厌其烦地讲述那片接近北极圈的荒原冻土地带上人们的真实生活,追索大自然和俄国民族的心灵。
《鱼王》一书是体现作家创作个性最充分的作品,这部取材于作家在西伯利亚的真实经历,讲述叶尼塞河流域的原住民和外来者的生活,集中体现了作家的道德观。这本书在苏联首版后获苏联国家文学奖,苏联国内报刊上围绕《鱼王》掀起了热烈讨论,阿斯塔菲耶夫被誉为“俄罗斯心灵的表达者”。
然而,作家本人却不喜欢这本书。《鱼王》的写作历程步履维艰,问世更困难,据阿斯塔菲耶夫回忆,“那时由于创作和校对手稿过于劳累”,他病倒住进医院。“但即使在医院里我也没有逃脱掉这倒霉‘鱼王’的纠缠”,他被编辑在电话里频繁地催促协调和补写段落,到半夜两点钟“还在通过电话‘创作’”。作品得奖后,他的写字台堆满了来自出版界和评论界的赞扬信件,其作品的首位鉴赏者,他的妻子谈起《鱼王》时却说:“你自己也不理解你写的是什么!”(见《最珍贵的稿酬》,收录进散文集《树号》)
《鱼王》问世后的某年十一月,他迁居回西伯利亚,独自和叶尼塞河天寒地冻的冷峭相处。一日归家,发现“门把手上挂着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几条鱼和一张纸条”,纸条上写着“送给《鱼王》作者。钓鱼人。”没有署名。
这张纸条让他“感到泪水开始湿润眼睛”,立刻决定邀请朋友来品尝鱼汤。“这是多么鲜美的鱼汤啊!”阿斯塔菲耶夫需要的,一直是普通读者。(见《鱼王历险记》)
《鱼王》与中国作家
作家王小波当时在读了《鱼王》之后说:“世间一切书中,我偏爱经过一番搏斗才写成者,哪怕是小说也不例外。这种书的出现,是作家对自己的胜利,是后辈作家对先辈作家的胜利,是新出的书对已有的书的胜利”,他将《鱼王》列入个人阅读中“不可多得的好书”。
《鱼王》由十三个中短篇故事构成。如果熟悉舍伍德·安德森的《小城畸人》或V·S·奈保尔的《米格尔街》和米沃什的《伊萨谷》的人,会看出它们之间的相似之处,都是作家基于自己的童年的生活地所经历的人事为蓝本创作的,《鱼王》写的是阿斯塔菲耶夫的故乡西伯利亚,那些居住叶尼塞河畔的亲戚,朋友和熟人,他用悲悯的笔触写出了这些人的喜怒哀乐。阅读这本书,你会看见里面有美丽的自然风景,个人记忆中的往事,还有生活在底层的,性格淳朴而默默无闻的小人物。《鱼王》情节其实非常简单,每个标题都是一个小小的事件,对里面的人物作者既不放过他们人性中的罪恶,也不会丢失同情的笔触。但每当在描写美丽的大自然的时候,作者都抑制不住内心油然而生的喜悦之情,在作者那里,只有自然是美好的,崇高的,甚至带着神性的气质,能够化解人类的一切丑恶,在那里所有人类都会获得天堂般的宁静。
对于《鱼王》这部作品表现出来的这种品质,或许不难理解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为什么中国现当代作家中很多人都深受其影响。比如藏族作家阿来把阿斯塔菲耶夫叫做“精神之夫”,他说:“其实我写小说最早是受《鱼王》的作者阿斯塔菲耶夫的影响”。阿来在主题上有很多和《鱼王》相似之处,比如在早年的创作中,短篇《已经消失的森林》就可以看出《鱼王》里人类对自然的掠夺的主题。
山东作家张炜深受《鱼王》在道德主题上的影响。他说《鱼王》“俄罗斯文学的伟大传统强有力地援助了它,它继续了它的余音,让其在冻土带上久久环绕。”张炜的部分早期作品如《九月寓言》《海边的风》,都同样关注在对自然肆无忌惮的破坏中的道德问题。
而对于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来说,《鱼王》对其影响更大,他在很多文章和外出演讲中提到过《鱼王》,对里面的片段常常能够大段背诵出来,他曾说:“我只记得他那里面写‘这是建设的年代,也是破坏的年代;这是在土地上播种农作物的年代,也是砍伐农作物的年代;这是撕裂的年代,也是缝纫的年代;这是战争的年代,也是和平的年代’等等”。
从《鱼王》对中国现当代作家的整体影响,可以看出,是里面存在的高于人类视野的道德力量,这种叫人反思的道德力量来自于大自然,阿斯塔菲耶夫曾说到:“我写有关大自然的作品既是为了孩子,也是为了成年人。我想让人们懂得:我们周围的一切,从绿色的草地到孱弱的小鸟,从原始森林里的野兽到种满庄稼的田野,直到我们赖以呼吸的天空和供给我们温暖的阳光——这一切的一切都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如果说这一思想在八十年代时契合了某种时代精神的话,那么在当今消费和信息高速传播的社会里,我们重新来读《鱼王》这部作品或许意义要更大。如果说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我们还能感受到《鱼王》里描写的美丽自然风景,那么面对现在城乡差距缩小的生活经验时,重读《鱼王》不仅有着道德教育的意义,还难免带上了乡愁的色彩。从这个意义上说阿斯塔菲耶夫犹如“大地之子”,带领我们在重温“俄罗斯田园颂”的时候,也警告我们人类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对自然的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