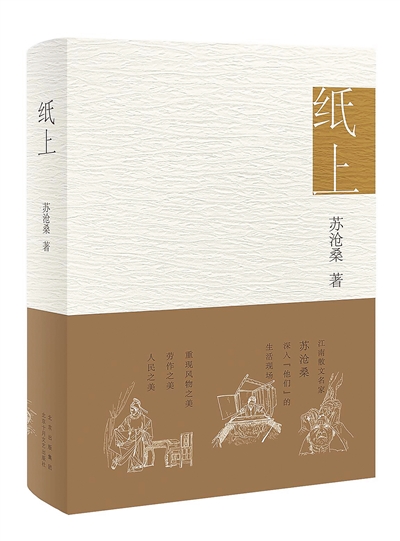文\本刊特约撰稿 傅菲
苏沧桑的散文集《纸上》置案头已月余,睡前读一篇,一个星期读完(七个单篇),复读而三。这是一本以描写蚕织、造纸、越剧、制茶、养蜂、酿酒、摇船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为主题的散文集,也是描写江南风物的别卷。
2016年,我写南方传统民间艺术为主题的散文集《木与刀》时,在浙赣鄂桂,历时一年,考察赣剧演变史、染布、造连史纸、制红茶、地方酿酒、南方木雕、傩舞,对诸多传统民间艺术的制造(生产)原理、现场、流程、工艺,有了更深的认知,也深深感知到我们的先人在工艺美学上,历经数百年甚至千年的积累,蕴藏着惊人的智慧,赋予了我们生活美学、古典工艺美学,滋养着我们一代又一代的人,即使在5G时代的今天,仍然散发无穷的魅力。因此,在我阅读《纸上》时,没有任何障碍,我很快也由“我”(作者)带入叙述的“角色”与“现场”:
矮矮壮壮的父亲放下砍竹刀,走到溪边,双手掬起溪水喝了几口,抹了把脸,向山脚望了望。晌午到了,该是女人送饭上山的时辰了。从小满到夏至一个月左右的时间,无论阴晴,朱家门村的后山上一直会回荡着当当当的砍竹声。(《纸上》P39)
为了写富阳逸古斋古法造纸,苏沧桑去了大源镇朱家门村,跟随造纸师傅一起上山砍毛竹。这个场景,我非常熟悉。造纸用竹,以一年新竹为佳,纤维细腻、含糖量低,此竹易泡浆、易槌丝、易团丝,造出来的纸,纸质柔软,吸墨饱满,不会被虫蛀。小满到夏至,新竹正好一年。砍竹人早上上山,傍晚下山,竹林之中砍竹声如啄木鸟分布竹丛筑巢。
在2019年夏季,我看到苏沧桑微信朋友圈晒出她在新疆奇台县草原和浙江养蜂人一起养蜂:戴着白色头纱(遮护面纱),裹着长长的白手套,端着巢框,蜜蜂围着她飞舞。这个场景很动人。我觉得她不像是来自浙江,而是来自古波斯。我想起她在2017年5期《人民文学》刊发的《纸上》,才恍然回神——苏沧桑在为一本书做准备,以数年之功,翻山越岭去生活的现场,聚焦于中华传统工艺。她给自己内心交代:集自己之大成,集江南风物之美,写出一本自己满意的书。这是她的执念。也是一个优秀作家必须要有的执念。执念就是生长力。竹笋没有执念,不会破土;种子没有执念,不会发芽;花苞没有执念,不会绽放;松树没有执念,不会挺拔。
6月25日,收到《纸上》。匆匆翻阅一遍,印证了我的想法。书的装帧、设计也美,古朴、简练、大方,符合我对一本好书的期待。也十分契合苏沧桑的气质。
《纸上》扑面而来的,是“我”始终在叙述的第一现场,工艺人始终在日常(生活与生产)的现场,“我”与工艺人不仅仅是叙述与被叙述的关系,更是情感互流的关系,“我”与叙述对象没有任何阻塞感。书中“涌现”出的大量丰沛细节,十分生动感人:
穿着长袍的七十岁的祖父打开一方干净的手帕,包上一只红彤彤的大蟹脚钳,装进裤兜里,慢悠悠穿过楚门南门街,走到十字街的西北角,踱进了楚门最大的烟糖公司杂货店,坐到了高高的柜台前。营业员小婶婶便浅浅一笑,转身去酒缸前舀上一碗酒,放在祖父面前。(《纸上》P256)
苏沧桑在《冬酿》中勾画的“祖父”,是她的祖父,也是我的祖父,还是你的祖父。爱酒的祖父,是南方小镇生活的缩影。一碗冬酿酒,美好的生活情调都在其中。
她写船娘:
西湖不动声色,盛着人世间无数悲欢,从不溢出来。西湖日日融化着千千万万个过客丢给它的心事,融化不了的,就化成了荷花、水鸟漂浮在水面上。多少年前,我在哪儿?多少年后,我在哪儿?西湖于我是永恒,我于西湖只是永恒之一瞬。这么一想,还有什么委屈是过不去的呢?
苏沧桑生活在西湖边,她懂船娘。在散文集《纸上》,字里行间流布着她的生活气息,追寻的气息。江浙是什么地方啊!制笔、丝绸、制茶、戏曲,发端或发轫之邦。她饱受古典文化、古典美学浸染。她的作品绵实而疏朗,古朴而典雅,端庄而开阔,醇柔而悠远,语浅而意深。
《纸上》是根植在大地的执念之作,根系发达,情感丰沛,她书写着大地之美,人情之美,生活之美,风物之美。她是大美之人。她是美的证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