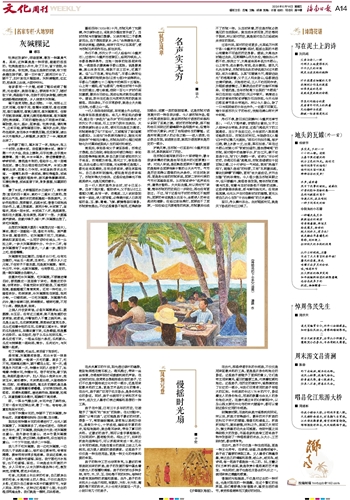■ 远人
嘉祐四年(1059年)十月,苏轼兄弟丁忧期满,作为新科进士,该赴京办理注官手续了。当时苏轼与苏辙皆已娶妻。父亲苏洵见二子都携家而出,自不想孤老家乡,决心“由荆楚走大梁,然后访吴越、适燕赵,徜徉于四方以忘其老”,便与苏轼兄弟同舟而出,前往京师。
舟行不停,苏氏父子一行人经渝州(今重庆市),过涪州(今重庆市涪陵区),经明月峡后,入丰都县靠岸停舟。当地一姓李的知县赶来相陪,一起登县内最高峰平都山览胜。说是最高峰,就山本身而言,海拔不足三百米,还真不高。但“山不在高,有仙则名”,平都山确有仙名,真宗朝的张君房在《云笈七签》中说得明白,平都山乃道教七十二福地中的第四十五福地。山上有一道观,名“仙都观”,传闻古时有个叫阴长生的道士,潜心修道,活到一百七十岁时仍面如童颜,最后白日成仙,其成仙地点就在仙都观中。据说,阴长生还是汉光武帝刘秀的阴皇后曾祖。因此缘由,不仅平常游客,就连士大夫路过此地,也都上山一观。
一行人刚刚走到观前,早有道士外出相迎,料是李知县提前通知。将几人带至观内游看间,道士在一块名为“金丹诀”的石刻前停步,对苏氏父子介绍说,石上文字乃阴长生亲刻。大约想获新科进士认同,便问石刻是否为真迹。苏轼简单答了句“不知也”,又顺笔写了首《留题仙都观》。从结句“泠然乘风驾浮云,超世无有我独存”中能充分看出,苏轼此刻的心理已彻底转化为对真实或现实人生的面对和肯定。
离观后,李知县将父子请至县衙。苏洵这才想起,自己刚到,李知县如何便已得知?李知县回答得神秘莫测,称自己数日前便知苏氏父子将至。苏洵颇为奇怪,再问之下,李知县告知,此处仙都山有只老鹿,无论野兽还是猎人,都无法将其捕获,当有远客前来,便在夜里鸣叫。自己连夜听到鹿鸣,便知是有远客来临了。苏轼听得大为惊异。这些沿途异事无不唤起其诗兴,也是见闻的增长。
当一行人再次登舟东去时,时令已至小寒。当夜下起大雪。雪助诗兴,父子拟以《江上值雪》为题,各写一诗。动笔前,三人谈到欧阳修有一说法,诗人若写雪,必得避开前人已然用滥的盐、玉、鹤、鹭鸶、飞絮、蝶舞等陈旧意象。苏轼索性提出,不仅这些意象不能用,还得剔除如皓白、洁素一类的陈腔滥调。这是苏轼对语言展开的一种自我训练。今人读苏轼作品,很少觉其语言陈旧,就说明苏轼对语言的实践和认识到了至高之境。彼时的苏轼诗歌,虽不能和他日后到达的巅峰期作品相提并论,但青年时的非凡意识,决定了他延续终生的攀越。这是所有真正诗人的必走之路——进入语言,也必然会发现,说语言古老,就因为语言原本是历史的一部分。
岁晚天寒,当苏轼一行至忠州(今重庆市忠县)时,果然就面对了历史。
在苏轼沿路写就的四十六首诗赋中,最令我读来震动的就是他写在忠州的《屈原塔》一诗。对后人来说,是否熟悉屈原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能体会屈原传承千载的士大夫气节。气节是历史观得以塑造的先决条件。对当时赴京师,更是赴仕途的苏轼来说,屈原二字所代表的气节对其感染至深。从苏轼该诗中“名声实无穷,富贵亦暂热。大夫知此理,所以持死节”来看,青年苏轼的历史观已一步到位,再也没有更改过。不过,写下这些句子时的苏轼还不能预料,屈原的命运就是从古至今,全部诗人的命运起点和缩影。没经过政治拷打,屈原成不了屈原,一如没经过天涯海角的流放,苏轼最后也成不了苏轼一样。从当时来看,历史是苏轼必然遇见的生活现实。就生活本质而言,历史等同于现实,所以面对历史,就是面对自己已经或尚未涉足的现实。
过忠州后,面对的史迹更多,尤其经万州武宁县(今重庆市武陵镇)西时,眼前出现的木枥山有着渺不可追的历史身影。据说,大禹治水时路过此处,见周围群山尽为水没,唯独此山木枥不动,惊异之下,大禹遂将其命名为木枥山。山上有寺,名白鹤寺;有观,名白鹤观。据孔凡礼先生考证,苏轼写在此处的诗名虽为《过木枥观》,实为白鹤观。从其“石壁高千尺,微踪远欲无”的落笔来看,父子三人均未登山,但都被远古情怀萦绕。天地苍茫间,三人不约而同作诗,为眼前缓缓横过,又飘然远去的旷古幽怀所感染。可惜的是,当年苏轼笔下出现的“木枥观”早已在后世(也是历史)风云中毁灭。晚清进士刘贞安曾将苏轼该诗镂为石刻存观,今天也早已移至奉节县白帝城内。所以今人登山,除了一口与观同修的千年古井外,一切都不可复见,唯千年前苏氏父子的咏叹,恍能在满山树叶声中听闻。
舟行不停,数日后已到夔州(今重庆市奉节县)。一行人下船休歇,安顿好女眷后,父子三人结伴访白帝庙、永安宫,这些乃闻名天下的三国遗迹。当父子走至江边,千年前的八阵图遗迹豁然在目。苏轼当时所见,与陆游在《入蜀记》中的记载几无差别,“碎石行列如引绳,每岁江涨,碛上水数十丈,比退,阵石如故。”早在过木枥山时就心怀“斩蛟如猛烈,提剑想崎岖”的苏轼,面对眼中的鱼腹平沙,旷古江天,禁不住思连千古,写下《八阵碛》一诗。该诗从“平沙何茫茫,仿佛见石蕝”起笔后,苏轼思绪便如千回百转之潮,三十行诗句一气呵成,既有“英雄不相下,祸难久连结”的忧愤,又有“孔明最后起,意欲扫群孽”的渴盼,更有“志大遂成迂,岁月去如瞥”的流年惆怅。今人很少提及苏轼早期之作,但只要翻开,就很容易发现,青年苏轼的激情与沉思,有着与当时年龄极不相称的成熟。这些诗歌虽涉典故,却与掉书袋无关。没有亲临其境,也无从产生对浩渺时空的感慨,更无从使自己内心生发“千古壮夔峡”的丈夫豪情。
翌日,舟从夔州东出。此时眼前所见,就是天下扬名的长江三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