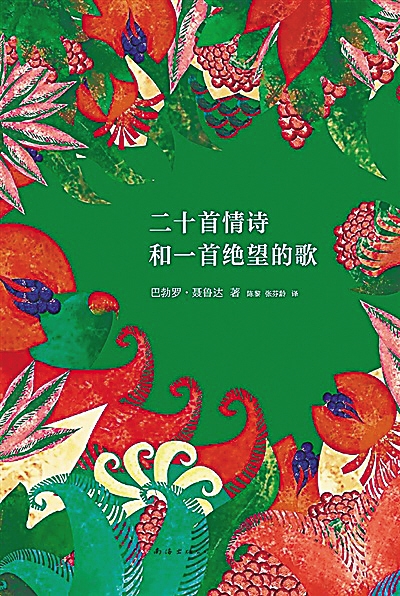■ 伊拉
智利诗人巴勃罗·聂鲁达一生有三个主题:爱情、诗歌和革命。在他69年的人生里,聂鲁达把这三个主题都演绎得淋漓尽致、无可挑剔。他也因此被视为拉美文学史上一位伟大的诗人。写出《百年孤独》的加西亚·马尔克斯既是聂鲁达的好友,也是他的头号粉丝。马尔克斯在《米格尔在智利的地下行动》中这样写道:“巴勃罗·聂鲁达在黑岛有一所房子,那里现今成了全世界恋人的圣地。诗人在世时,这里住满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年轻人,他们手中唯一的导游书就是聂鲁达的《二十首情诗》。”而在评价作为诗人的聂鲁达时,马尔克斯全是赞美之词:“巴勃罗·聂鲁达是20世纪所有语种中最伟大的诗人。他书写任何事物都有伟大的诗篇,就好像弥达斯王,凡他触摸的东西,都会变成诗歌。”
今年7月12日,是聂鲁达诞辰120周年。今年离聂鲁达代表作《二十首情诗和一首绝望的歌》的出版,也整整100年了。世界各地都在举行纪念活动,仿佛整个世界都是诗歌和爱情的栖息地。
面包里的十四行诗
1904年7月12日,聂鲁达出生于智利帕拉尔城一个很普通的家庭里,在他满月时,母亲就去世了。身为铁路工人的父亲是一位严父,他并不懂诗,在读了少年聂鲁达写的第一首诗后,他冷冰冰地评论道:“这是你从哪里抄来的?” 这一句评论大概对少年的打击并不小,因为在16岁时,为了不让父亲看到自己发表的作品,这位少年作家开始用“聂鲁达”这个笔名,取自他崇拜的捷克诗人扬·聂鲁达。
童年时期的聂鲁达和家人住在智利南方潮湿的森林边。早前,他的父亲当过农民和大坝工人,但都过于平庸,但最终,他在附近的铁路上成了一名优秀的火车司机,此时这位父亲的心情不错,忙于运输沙石时,他还把小聂鲁达拽出学校陪他开车。他们穿行在森林里,小聂鲁达因此见识了无数“瑰丽的珍宝”:高大的蕨类植物、五彩甲虫、野鸟蛋……在雨水与被藤蔓吞没的树干中,这个善感的小男孩,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爱,他爱上了这个充满奇迹的世界。事实上,他很少在情诗中直白地说“爱”,而是将恋人看作他爱的蜜蜂、海螺、李子、落叶松、烟与穗子。年幼时在森林里的经历,似乎是世界特意赋予他爱的表达。
聂鲁达大概是这个世界上最懂得爱与生活的人。从他的自传里,我们看到他把爱情放进了诗行和面包。他狂热地爱着诗歌和食物,在某次难得的自助餐宴会中,他往盘子里堆起诡异食物的小山:“奇特的鱼、难以描绘的蛋、意想不到的蔬菜、说不明白的童子鸡、罕见的肉,像旗帜似的盖在我午餐山峰的顶上。”在《一百首爱的十四行诗》中,他不断地用面包向恋人示爱;在《漫歌》中,他七十七次提到“面包”,还在最尽兴的结尾部分突然说起美酒、鲜鱼、腌兔。因为体重超标,妻子严格控制他摄入糖分,诗人愤怒地回应:“我要吃掉所有甜瓜,直到我变成一个甜瓜。”
于聂鲁达而言,吃,是人生的大事。他说:“与诗歌最相似的东西,是一块面包,或是一个瓷盘,或是满怀柔情地加工过的一段木头。”而他的老朋友马尔克斯在诺贝尔奖晚宴上提起聂鲁达时,隔空进行了鸣鹤之应:“诗歌是平凡生活中的神秘能量,可以烹熟食物,点燃爱火,任人幻想。”
面朝大海呼唤艾青
在《我坦言我曾历尽沧桑》的题记里,聂鲁达说:“我的生活丰富多彩。”他没有夸张。南美大陆向来充满激情和戏剧性,于我们而言,这是一块以“魔幻现实”著称的土地,而聂鲁达就在这样的土壤里长大。
他是一位外交官,出任过智利驻多个国家的领事,走遍了大半个地球,见过了无数的风景。他在锡兰(今斯里兰卡)驯养了一只灵巧的獴,又不幸在巴达维雅(今印尼首都雅加达)遗失了它;1941年他任智利驻墨西哥总领事时,曾接待过7个想以最快速度离开墨西哥的日本人,他感觉他们不对劲儿,拒绝给他们发放签证。一周后,珍珠港事件爆发……
他曾奋不顾身地将2000名西班牙难民送往智利,让他们远离西班牙内战的战火;他曾被选为国会议员,然后不得不流亡海外;他曾被智利共产党推荐为总统候选人,后来则出任智利驻法国大使……他一生都在战斗,各种各样的战斗。被流放、被驱逐、被逮捕,被意大利警察送上火车,又被激动的人群抢回来;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躺在担架上被抬走,旋即又因人们的联名呼吁而释放;酒吧里打架的黑帮老大拦住他,眼含热泪朗诵起他的诗句;在集会中呐喊的人群一见到他上台,便纷纷脱帽致敬……
他与中国的缘分,也是极其奇妙的。他一生来过三次中国,并见证了中国的新生。他在《我坦言我曾历尽沧桑》中提及了自己的三次中国之旅。1928年,他曾途经上海。1951年,当他再次访问中国时,看到的“已是一个崭新的国家”,他说:“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化在广大土地上雄辩地发生了变化……中国人是世界上最爱笑的人……没有任何一个民族比他们更懂得笑。”接待他的中国作家们也以真诚、美好的笑与他一路同行,其中,就有诗人艾青。
聂鲁达与艾青之间确有很深的机缘。1954年,艾青受邀赴智利庆祝聂鲁达50岁的生日,因当时国际形势复杂,艾青不能直接飞往智利,后取道亚洲、欧洲、非洲,最终来到南美的智利。这趟旅行,艾青走了整整2个月,他把这两个月称作“从夏天赶往冬天”的旅途。
因为艾青的这趟传奇之旅,两位诗人迅速成了好友,并常作鸣鹤之应。1957年,聂鲁达再访中国时,便由艾青陪伴游览。当聂鲁达寻找艾青时,他会对着大海呼唤艾青的名字。值得一提的是,在这趟中国之旅中,聂鲁达以诗人之眼关注忙于耕种的人们:“在极高处,在壁立的岩石之巅,一个褶皱里只要有点儿生长植物的土壤,就有中国人在那里耕种。”他也因此对中国充满信心:“辽阔的土地,人的非凡劳动,一切不公正现象的逐步消除,这三者的结合一定能使中国人美好、广阔而深厚的人性更加发展。”
复苏一个大陆的梦想
在自传《我坦言我曾历尽沧桑》中,聂鲁达本人这样描述自己:“我是杂食动物,吞食感情、生物、书籍、事件和争斗。我真想把整个大地吞下。我真想把大海喝干。”
于聂鲁达而言,这些话不是某种修辞,而是他实实在在身体力行的事。他一辈子都在竭尽全力“吞食”一切,就像一只永远不知餍足的巨兽。
他的一生,比烈焰更灼热,尺幅甚至比大海还更宽广。他的人生,甚至比诗歌更富诗意。
每一个试图去写他的人,大概在写作的过程中,都会产生强烈的自卑感:他19岁出版第一部诗集;20岁凭借《二十首情诗和一首绝望的歌》享誉世界,那些美妙的语句总是令人悸动:我们甚至遗失了暮色。/没有人看见我们今晚手牵手/而蓝色的夜落在世上。/……永远,永远,你退入夜晚/向着暮色抹去雕像的地方。
聂鲁达23岁开启外交生涯,被派驻缅甸仰光任领事,在此后7年间先后赴锡兰(斯里兰卡)、科伦坡、新加坡、印度尼西亚等国担任领事;25岁完成诗集《居留在大地上》……也许,这一切,都来源于那片光怪陆离的智利大森林。
而后,大海将他带向了更为广袤的世界。大海是沉静的,狂怒的,亦是多变诡谲的,聂鲁达似乎深得大海的真传。29岁时,他被派驻西班牙巴塞罗那任领事,这是他人生的转折点。而他人生的高潮,在他30岁时就早早地到来。西班牙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他说:“西班牙是一列长得没有尽头的火车。”
他和朋友们一起诗酒狂欢,一起筹办承载血与火的诗刊,一起投身于西班牙内战、为自由奔走,一起经历二战的残酷悲怆。其间,他选定了一条路,并毕生践行自己的政治理想。他说:“世界变了,我的诗也变了。有一滴血在这些诗篇上,将永远存在,不可磨灭,一如爱。”
在《我坦言我曾历尽沧桑》中,聂鲁达以记忆碎片的形式,将自己的一生缓缓铺陈,映照出一段举足轻重的历史。他说:“但愿生命,还有世间的快乐和痛苦,每天都能推倒房门,进驻我们的房子。”
1971年,瑞典文学院宣布授予聂鲁达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词是:“他的诗歌具有自然力般的作用,复苏了一个大陆的命运与梦想。”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