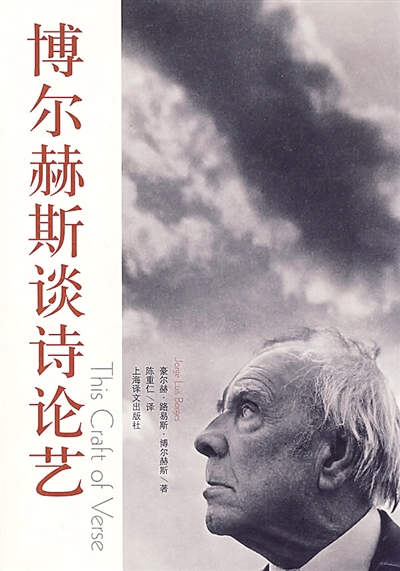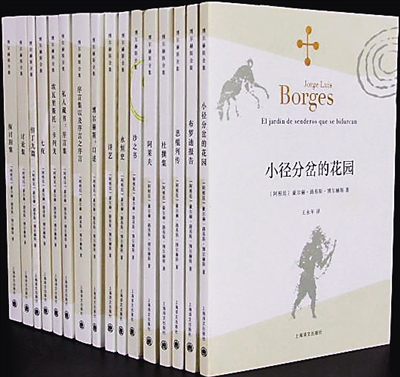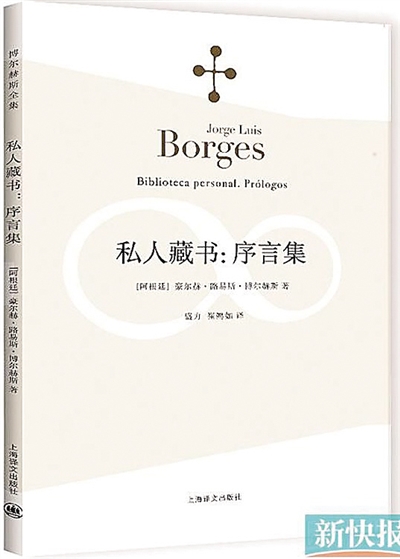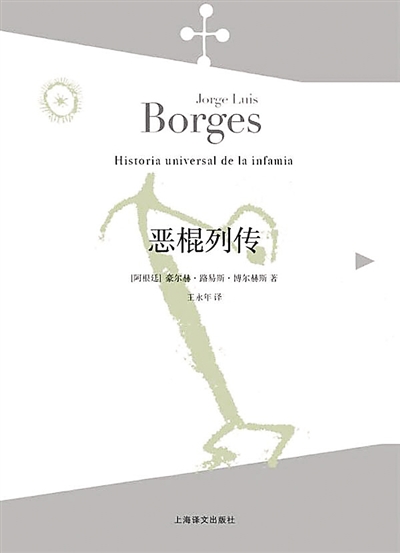他失明时,靠中国拐杖行走
博尔赫斯,这座迷宫的时间入口还要从1946年说起。这一年,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街头,马黛茶的芳香与伦巴舞的曼妙突然冷却了,取而代之的是弥漫起了波诡云谲的政治氛围。一个叫作庇隆的军官通过军事政变僭越为阿根廷的主宰者,博尔赫斯却因为批评了这位政坛新贵,被革除了布宜诺斯艾利斯市立图书馆馆长的职务。颇为羞辱的是,他的下一份工作居然是被勒令去当家禽检疫员。命运总是擅长捉弄人,等到了1955年,它又把玩笑反转之后再度戏弄两位当事人。曾经依靠政变上台的庇隆,最终因为贪腐而被他的继任者用同样的方式推翻。此时,鸡棚里的大作家已经难以亲眼“目睹”此情此景了——这位嗜书如命的人眼疾加剧,几近失明——就在听闻庇隆主义即将消失于阿根廷官方意识形态之后没多久,他终于又得以回到他的图书馆了。只不过,这一次不是市立的,而是因祸得福地成为了国立图书馆馆长。
可是,博尔赫斯平反复职的激动心情尚未消褪,他就不得不面临“卡珊德拉困境”——古希腊神话里,神赋予了卡珊德拉预言未来的能力,但同时又限定没有人会相信她的预言。他曾说,“如果有天堂,天堂应该是图书馆的模样”,后来他失明了,这位天堂里的瞽叟只好自嘲地叹息,“命运赐予我80万册图书,由我掌管,同时却又给了我黑暗”。
在失明的日子里,博尔赫斯经常要依靠一根来自中国的漆器拐杖来行走。尽管有人统计,在他的全集里总共有多达37次提到了“中国”,但是行动不便的他再也无力前往这个曾在各种古籍里多次读到并诱发他产生无限遐思的古老国度。的确,终其一生,博尔赫斯都未踏足那根拐杖的故乡。此时,命运再一次用一种曲折的方式弥补了他。1961年,博尔赫斯荣获了第一个国际性文学奖项,他和荒谬派戏剧大师塞缪尔·贝克特分享了国际出版家协会设立的福门托文学奖。凭借着这一殊荣,他的名字得以远渡重洋,在中国秘密靠岸。只是,就如同走私一样,他的名字被乔装成了“波尔赫斯”,首次出现在《世界文学》期刊某个不起眼的角落里。
他的作品,永别诺贝尔文学奖
此后,他的名字来到了中国,可是并没有多少人知道他。直到1979年,他终于不再被当时的文学期刊拒之门外了。该年度首期《外国文艺》杂志上,刊登了王央乐翻译的《交叉小径的花园》等四篇短篇小说。此后数年,王央乐在此基础上又翻译了数篇,在1983年集结成册为《博尔赫斯短篇小说集》,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发行。
1976年,博尔赫斯彻底断送了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机会。原因是他即将赶赴智利,接受独裁者皮诺切特颁发给他的贝尔纳多·奥希金斯大十字勋章。据他的遗孀玛丽亚·儿玉事后回忆,正当他打算出发之时,意外地接到了从斯德哥尔摩打来的电话,一位参与评选诺贝尔文学奖的瑞典皇家文学院人士向他表达善意的建议,希望他取消行程。然而,博尔赫斯只是在电话里礼貌地对他表示了感谢,却态度坚决地表示“去智利是我的责任”,并且反诘对方说:“有两件事情,人是不该做的:行贿和受贿”。言外之意似乎是在暗示,对方有意用诺贝尔文学奖行贿他,以使他不去智利。事后,瑞典文学院院士阿瑟·伦德克维斯特就此事公开表态,正是接受皮诺切特的授勋让博尔赫斯和诺贝尔文学奖永别了。博尔赫斯自然也不甘示弱,他则对此评论说,“获奖只可用来满足虚荣心;既然是为了满足虚荣心,不得诺贝尔奖也罢”。
他的小说,曾是中国作家的 “描红簿”
不过,在登临文学巅峰的路上受阻,并未影响到他在中国的传播。对于忠实拥趸来说,未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并不足以弱化博尔赫斯的文学地位。不妨开具一份未获诺奖的20世纪文学大师清单,赫然在列的还有普鲁斯特、乔伊斯、卡夫卡、卡尔维诺……很难说获奖阵营和未获奖阵营孰优孰劣。这一次,运气终于站在了博尔赫斯一边。至少在中国,他比大部分的诺奖获得者都生逢其时。他在中国的首度正式亮相适逢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学热潮,马原、格非、余华、苏童等先锋作家相继涌现。博尔赫斯的文风在叙事上有着鬼魅而绚丽的技巧,迅速赢得了文学青年的追捧。然而,在那个资讯欠发达的年代,一本惊世骇俗的小说无异于一册江湖上竞相争夺的武林秘籍。对于博尔赫斯,文学青年们狡黠地秘而不宣,避而不谈,希望能够把他变成可以垄断的隐秘资源。因此,他的声名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反而仅限于小众化的文学团体。直到近年,一份如何正确使用博尔赫斯的档案才被解密公开。据称,当时不少尚未成名的作家几乎把他的小说视为“描红簿”,写作时总在书桌上摊开一册《博尔赫斯短篇小说集》,但凡灵感枯竭、语词堵塞,就随意翻开一页,临摹上几句博尔赫斯的句子,自然而然就能文思泉涌。不论是被定义为抄袭也好,借鉴也罢,客观而言,这种早期仿造性的生产模式奠定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先锋文学的话语品质。其影响之深,甚至一直要波及到上世纪九十年代末。
可惜,同样的剧本再度上演时,依旧是“卡珊德拉困境”的命运作祟。正当博尔赫斯的声名在中国文学界不断兴盛,他本人却再也听不到这一喜讯了。1986年6月14日,晚年旅居瑞士日内瓦的博尔赫斯,因为肝癌医治无效而去世。他的“新婚”妻子玛利亚·儿玉仅仅在两个月的蜜月之后就变成了遗孀。儿玉成了博尔赫斯的文学遗产继承人。1999年,在她的促成下,“博尔赫斯全集”以5万美元的低价版权费交付给了浙江文艺出版社。姑且撇开当时中国社会的平均购买力,仅从国际出版业的行价来看,如此低廉的版税简直难以匹配博尔赫斯的大师身份。况且,这笔费用还要用以支付她前来中国洽谈相关事宜时的路费,最终也所剩无多,足以可见此举多少有些类似于慈善性地半卖半赠了博尔赫斯的部分文学遗产。
值得一提的是,儿玉的中国之行特意前往了博尔赫斯小说里提及的秦始皇兵马俑和长城。她凝视着秦俑的身躯,抚摸着长城的砖墙,见证了亡夫只在想象中才能够一瞥的景象。或许,博尔赫斯泉下有知的话,他应该感到欣慰,比起肉身的永生,活在文学里并且享有长久的声誉才是他的理想;比起肉身短暂地抵达中国,一套《博尔赫斯全集》在中国的发行才是以文学之名在中国永生。
当然,严格说来,浙江文艺版的《博尔赫斯全集》,可谓是“全集不全”,并未收录《想象中的动物》等作品,至多算是“局部的永生”。这个遗憾直到2012年才获得了弥补的一线曙光。上海译文出版社对外宣称将补齐散佚的博尔赫斯作品,重新出版名副其实的全集。这一次,似乎又是好事多磨的宿命。不知何故,此事延宕了三年仍未见落实。经过了漫长的等待后,最近,新版《博尔赫斯全集》终于正式发行。这样的故事多少也颇为符合他小说里的曲折情节,只不过,就如同分叉的小径全都汇聚到主干道上一样,伴随着这次真正意义上的全集问世,博尔赫斯在中国的文学传播历史也渐渐趋近于一个完满的终点了。
关于博尔赫斯
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 1899年8月24日-1986年6月14日),阿根廷诗人、小说家、散文家兼翻译家,被誉为作家中的考古学家。生于布宜诺斯艾利斯一个有英国血统的律师家庭。在日内瓦上中学,在剑桥读大学。掌握英、法、德等多国文字。 作品涵盖多个文学范畴,包括:短文、随笔小品、诗、文学评论、翻译文学。其中以拉丁文隽永的文字和深刻的哲理见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