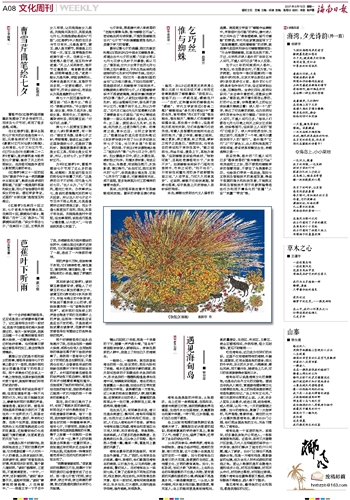■ 颜小烟
有一个会讲故事的曾祖母,这应该是我小时候最幸福的事了。记忆里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是守在曾祖母的柴火垛旁度过的。每天一放学回来,我就立刻搬一个小板凳到曾祖母的柴火垛旁,一边看她劈柴火,一边听她讲故事。任何故事只要经过曾祖母的加工,就会变得异常精彩。
最难以忘记的是牛郎和织女的故事,曾祖母说每年七夕的晚上都会下一场雨,那是牛郎和织女因重逢而留下的相思之泪。那个夜晚他们还会说上一个晚上悄悄话,如果你躲在芭蕉叶底下偷听,就能听清他们所有的谈话内容。
我对曾祖母的说法深信不疑,但我知道偷听是一种不光明的行为,所以我只能躺在床上,静静地听雨打芭蕉的声音,滴滴答答,直到天明。曾祖母用她温柔的嗓音为我打开了通往另一个世界的大门,那里住着善良、慈悲、美好、神奇和幻想。在那个世界里,我能看到祝英台义无反顾地跳进梁山伯的坟墓里,还能看到他们化成蹁跹飞舞的蝴蝶,往更高更远的天空飞去……
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深深地迷恋上了雨打芭蕉的声音,它仿佛象征着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情语,从深夜说到天明。后来读宋词,读到“有谁知我此时情,枕前泪共阶前雨,隔个窗儿滴到明。”读到“梧桐树,三更雨,不道离情更苦。一叶叶,一声声,空阶滴到明。”读到“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读到“萧萧疏雨滴梧桐。人在绮窗中。”……那些文字一下子击中了我,仿佛曾祖母为我所描绘的世界中,也曾出现过无数次这样的雨,它们和我童年里的雨滴到了一起,连成了一片绮丽的海洋。
雨的声音千万种,我独钟情于夜雨,它们绵绵密密,滴在屋瓦,滴在树梢,滴在窗台,像一首首轻柔的小夜曲,滴进了梦境的森林。
再后来读《红楼梦》,读到黛玉教香菱写诗,便陷入了对黛玉的无以复加的喜欢之中。读黛玉的《葬花词》《秋风秋雨夕》,听她与湘云的中秋联诗,听她说不喜欢李义山的诗,却独独喜欢那一句“留得残荷听雨声”。或许雨打在残荷上的声音会稍逊于雨打在芭蕉叶上的声音,但那样一种情思应该是亘古不变的吧。于是我便开始试着去读唐诗,在唐诗中感受曾祖母没有描绘过的各种各样的雨声。
那个时候曾祖母已经永远地离开了我,当我坐在那一堆柴火垛旁,却再也没有人会用她那样的嗓音在椰子树下给我讲故事了。虽然那一场每年七夕都会下的雨还是会如期而至,只是再也没有人会像曾祖母说的那样躲在芭蕉叶下听牛郎织女耳语了。乡村里的故事在曾祖母的绘声绘色下悠远绵长,曾祖母的年岁也随着故事越拉越长。当她结束了她的所有时间,当我站在她的棺木前,我依然希望自己能再一次打开她的那一个神奇的故事盒子。
现在,我们早已离开了乡村,住到了钢筋水泥的森林里,听雨在这个时代渐渐变成了一件极度奢侈的事情。每下一场雨,我所能听到的也只是雨落在窗台时的那一种窸窸窣窣声。每年七夕,只要有雨,我就会想起曾祖母在庭院里摆起的长凳,凳子上放着一个空碗和一双筷子,七夕夜一过,凳子上的空碗里就会积聚起一定量的雨水。我知道这样的雨水还会经年累月地出现,可是那样一种清凉的感觉却早已在时光的流淌中不知去向了。
“芭蕉滴滴窗前雨。”老家屋后的芭蕉树已不在,芭蕉叶下听雨的美好已经慢慢变成了过去时。那一场七夕落下的雨,穿过唐诗,穿过宋词,穿过淋漓的梦境,抵达的是通向美好未来的心灵秘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