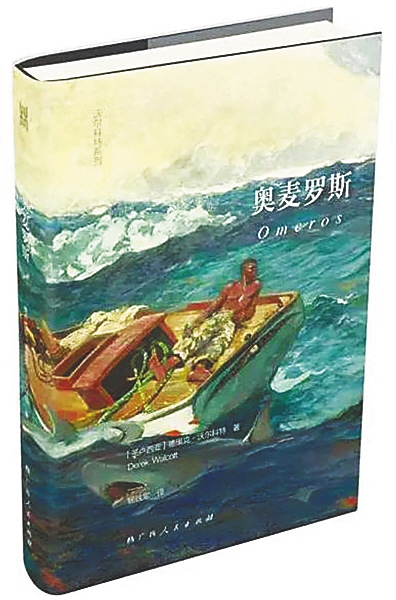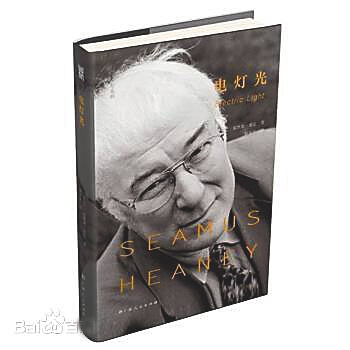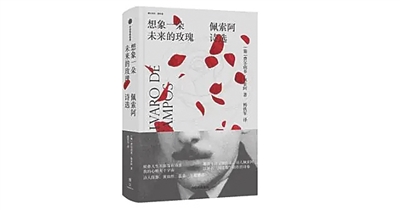文\海南日报记者 杨道
8月25日,诗人、翻译家杨铁军凭其译作《奥麦罗斯》荣获第八届鲁迅文学奖翻译奖。
《奥麦罗斯》是199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圣卢西亚诗人沃尔科特的一部现代史诗巨构,被国内诗歌翻译界称为“最难翻译的作品”。“奥麦罗斯”为古希腊长篇史诗《荷马史诗》的希腊语译名,全书以当代为坐标,上下五百年,在空间和历史中自由穿梭,把殖民历史、个人记忆、希腊神话、现实政治、加勒比海地区的生活经验交织成一体。作者以一种奇幻的后现代手法,给这部有着厚重历史底子的作品赋予一种广阔的诗意空间。而译者杨铁军,多年来一直致力于推动外国诗歌在中国的译介与传播,不断拓宽国内读者的文学边界,让读者得以领略世界文学的魅力。他用极富表现力的语言,赋予原作以穿透时空的生命力及艺术感染力。
9月23日,杨铁军接受了海南日报记者的专访。
翻译界最难翻译的作品
记者:据说《奥麦罗斯》是翻译界最难翻译的作品。您翻译它的初衷是什么?
杨铁军:确实,《奥麦罗斯》的篇幅过于庞大,名声太响,人们都是隔一层神秘的面纱来眺望它,很难有一个客观的认识。我也是因此一开始不想接手,拒绝了编辑的邀约,但后来我想通了,决定还是要迎接挑战。因为一直以来,我做翻译都是抱着学习的目的,挑战越大,学到的东西也就越多,对自己的写作就越有帮助。所以,我无法拒绝这个巨大的“诱惑”。
记者:在翻译过程中,都遇到了哪些困难?您是如何解决的?
杨铁军:我对《奥麦罗斯》的难度有一定的预期,但也没想到其难度远超一开始的预期。难度其实并不在对原文的理解,或对作者的海洋背景的理解上,而是在于如何把一部杰作,从一个语言中转移到另一个语言之后,也能是一部杰作,至少能让读者透过字里行间,对原作的风采能有一定的体会,而这已经是最低目标了。
我仔细考虑过可资利用的语言资源,但能想到的许多文本后来都被我一一否定了,因为翻译是有时代性的,应该用活的语言来进行。最后,在反复思考无果之后,只能一头扎进去,在游泳中学习游泳。但我没想到自己扎进去的是汪洋大海,因为没有大方向,所以每一行都面临困难的抉择,疲于应付,抬不起头来,每有绝望之感,不止一次想到放弃。在纪律性的约束下,完成了全书的初稿。但是完全没有喜悦,只有深深的沮丧和怀疑。
搁置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开始修订,花了很长时间,反复修改前面几个章节,不下六七十遍,切磋琢磨,最后终于找到了我脑海中的那个声音,内心感到强烈的喜悦,但更多的还是庆幸,因为一切看似偶然,我却体会到冥冥之中的必然。
大海已经进入沃尔科特的血液
记者:自然风景是《奥麦罗斯》的大背景。您说过,从沃尔科特的语调中可以听到大海的轰响?
杨铁军:风景不是可有可无的点缀,它不光是《奥麦罗斯》的大背景,隐居幕后,而是直接踏上舞台,参与了故事进程,是贯穿这部长篇史诗的决定性的力量。所有的人物、情节、事件都围绕着大海进行,即使在作者游历欧洲和北美大陆的时候,大海也从来没有缺席,因为大海已经进入沃尔科特的血液,所以自然而然地从他的声音里流露出来。
《奥麦罗斯》的最后一句话说:“他离开海岸的时候,大海还在那里咆哮。”如果说,一切的矛盾都酝酿于大海的轰响,那么最符合逻辑的结论是,矛盾的解决、与生命的和解也只能从大海的轰响中寻求,沃尔科特正是这么做的。一方面,这个结局出乎预料,因为读者期待更戏剧化的解决,另一方面,这也符合预期,因为这也是唯一的可能。永不止息的大海推动情节的发展和矛盾的解决,蕴含了生命的真理,是加勒比海人讨生活的“土地”,是他们的舞台,也是他们的命运。
记者:沃尔科特将加勒比海比作一个重新发明斧头的地方,听起来有一种披荆斩棘的感觉?
杨铁军:沃尔科特的意思是说,加勒比海是一个没有文化传统的地方,一个作家举目四望,发现处处荒凉,没有悠久传统的负担,你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有起源的意味,拿起斧头砍树,并不是世世代代的伐木工人肢体动作的重复,而是像伊甸园里的亚当那样,劈下了人类的第一斧,具有象征意义。
这种看法很有意思,一般来说,作家会抱怨传统的缺失,进而否定自己的现实和文化,好像没有传统的现实不是现实,没有传统的文学不是文学,因而对远方的文学艳羡不止;沃尔科特却反其道而行之,他在荒漠中看到的不是贫乏,他所说的每一个词,都有原初的意味。
沃尔科特在《奥麦罗斯》中认识到,加勒比海不需要进入欧洲的象征系统,如果加勒比海始终停留在用一个他者的眼光来观照自己的模式中,那么无论加勒比海的生活多么热烈,都产生不了“意义”。
诗人译者要摆脱“含混”的诗学认识
记者:在国内,有不少翻译家的另一身份是诗人,这两者之间有什么特殊的联系吗?
杨铁军:诗人译诗有自己的优势。一般来说,诗人对汉语诗歌语言的把握比较好,可以呈现较好的汉语。不会译成顺口溜,或者押乱七八糟的韵。但诗人译诗,特别是在国内,容易犯一个错误,即认为诗就是要让人看不懂的,译文如果谁都能看懂,就不是诗了。包括很多读者对现代诗也有类似的期待。
这其实是一个误解,因为绝大部分诗,几乎没有例外,在原文中都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意义上是非常准确的,不容含糊。我们诗人译者应该早日摆脱“含混”的诗学认识,把握原文的逻辑线,不要满足于“朦胧”的美学借口,才能翻译出较好的诗歌。
记者:从1992年的诺奖受奖词中可以看出,沃尔科特对加勒比海文学的独立性很在乎?
杨铁军:沃尔科特是说,加勒比海人是文盲,不识字,就好像树叶不识字一样,他们不读,只能被读,如果他们被人以适当方式阅读了,那么他们就可以创造出自己的文学。沃尔科特认为加勒比海地区的人们并不是不懂得生活,也不是创造不出自己的文学,他们是世界上最乐观、最热烈、最懂得投入生活、最有创造力的人,但是在欧洲文学的观照下,他们却只是某种“忧郁”的西方心理的投射,他们只能是碎片、某种“失去”、某种“乡愁”,而不能作为完整的“文明人”而存在。从西方人的眼光看来,他们的生活不是生活,因为他们一无所有,更重要的是,他们无法进入历史。沃尔科特认为这样的历史不要也罢,因为历史只能发生在废墟之上。加勒比海的人同样也在生活,和欧洲人一样,但是不产生文明的废墟,这需要一种全新的叙述,全新的文学。
记者:您是沉潜于文学世界的芮城诗人。曾辗转多地求学、深造,从芮城到北京到美国再回归家乡芮城,有一种中国文化传统“落叶归根”的情结。您如何看待自己的这份“漂泊”?它对于构建您的文学世界有怎样的影响?
杨铁军:我内心一直有一种挥之不去的漂泊感,总感觉自己是异乡人、局外人。在美国求学期间,我上学路上会经过一座小桥,桥下流着蓝蓝的水,但我总是强迫症一样在心里对自己说,梁园虽好,跟你都没关系。后来到了亚特兰大,我的房子里家徒四壁,连个沙发都没有置办,因为我总觉得我只是暂居,但却没想到一待就是那么多年。
有时候我自己也会想,这是为什么?最直接的原因当然是身处异国他乡,更容易有离家的感慨。但从一个写作者的角度,我也为自己的漂泊感找到了依据,或者安慰,因为写作者必须能跳出自己,从自己之外观照自己,这是一种内在于写作行为的割裂,一种必然的漂泊。如果更进一步,从一个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角度出发来看问题,那么自五四以来,现代性话语逐渐替换了中国传统的知识系统,把知识从“本地”剥离了,一个知识者的成长必然意味着背离故土,去大城市,去异国他乡,走得越远越好。所以,漂泊是知识的必然命运。你必须以某种方式接受,并与之和解,就像沃尔科特必须从大海寻求和解一样。
诗人档案
杨铁军1970年出生于山西芮城县南磑镇大禹渡村,辗转多地求学、深造,从芮城到北京到美国再回归家乡芮城,主要从事英语文学翻译与诗歌创作。译著众多,他翻译的《想象一朵未来的玫瑰·佩索阿诗选》获选2019年深圳读书月“年度十大好书”,《奥麦罗斯》获得2019年袁可嘉诗歌奖·翻译奖、第八届鲁迅文学奖翻译奖。
本版图片由受访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