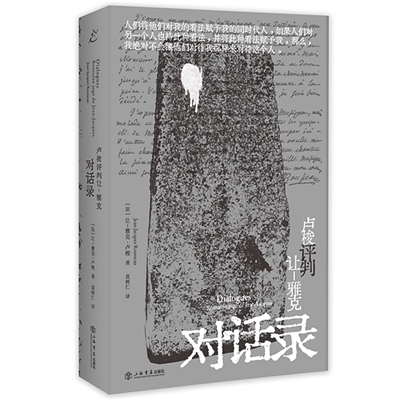■ 杨道
《卢梭评判让-雅克:对话录》(以下简称《对话录》)是我近年来读过的感受最奇特的一本书,这使我有一种急需与他人分享的迫切感。
《对话录》写于1772年—1776年,是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后期的重要作品,与《忏悔录》《漫步遐想录》一起并称为卢梭晚年三部曲。但在我的认知里,《对话录》要比后两者的知名度差了许多。这或许缘于卢梭当时的境遇:他的著作《爱弥儿》成为禁书,《忏悔录》被禁止朗读,反对者的攻击使他声名狼藉。
在《对话录》中,卢梭将自己一分为二:“卢梭”和“让-雅克”,由饱含探知欲的“卢梭”和人云亦云的“法国人”就受到污蔑的“让-雅克”的品格、作品与思想展开三次对话,实际上是卢梭针对自己遭遇的种种不公正对待展开的全面辩护,书中充满矛盾和断裂,一如历史迷雾中的卢梭本人。
法国哲学家福柯曾将《对话录》称为“反忏悔录”。这个“反”不仅仅是形式上的。在书中,卢梭不得不正视、复述关于自己的指控,写下自贬之词,再从旁观者的角度为自己正名。
在阅读《对话录》的过程中,我会随时想起《忏悔录》中的一些词句,两者类似于性情迥异的孪生兄弟,本质上都是自辩,然而,两者的差异又是极其明显的。在《忏悔录》中,卢梭采取的是以退为进、以守为攻的策略,他把想要说的一切都说出来,无论是好的一面还是坏的一面。但《忏悔录》写完之后,读者并没有领情,没有透过他的伤疤看到他的善良,而是集体保持沉默。这让卢梭感到非常难堪,他十分失望,便没有继续续写《忏悔录》。故而,在《对话录》中,他改变了《忏悔录》中独白的叙事方式,而改用分析的论辩方式。
值得一提的是,在《对话录》中,卢梭把自己(即“让-雅克”)设定成一个未知数,然后从正和反两方面进行求解。
就文体而言,《对话录》是一部四不像的作品。它似乎是一部自传,但又不像自传。卢梭写的是自己,然而,除了名字,那些内容场景完全是虚构的,且内文中所述事实极少。此外,书中的对话,颇有戏剧感,但戏剧是由对话构成的,而《对话录》在语言上毫无口语的短促句式,在内容上也缺乏足够的情节和冲突。更令人惊诧的是,一个人的对白居然能长达三五页,最长的虚构场景,卢梭一口气说了三十多页,里面充斥着大段的卢梭哲学思想论述。这使得该书的阅读过程就像在跋涉,此时的观感就像是在研究一部论著作品。
在《对话录》中,人物、情节、内容都非常简单。书里的对话形式,并无特别之处,但用对话写自己,比较罕见。有研究卢梭的专家称,卢梭选择这种形式,是因为他不得不战,不得不论。这和他晚年的一个心结有关,就是阴谋。阴谋是卢梭晚年一个解不开的心结。因为卢梭经历了八年的流亡,他感到一张大网在向他张开,他的敌人无时无刻不在歪曲和诋毁他的形象。这个阴谋是默契的、沉默的、无言的。事实上,《对话录》从头到尾充斥着对于阴谋的反复描写。
一直置身于阴谋阴影中的卢梭,沉默贯穿于他的作品中,譬如《忏悔录》是以沉默结束的,而《对话录》以沉默开始。沉默是《对话录》写作的动因。
在《对话录》的开头,卢梭发表言论,称那深不可测人人守口如瓶的沉默,就像他所包裹着的秘密一样,匪夷所思。十五年来,人们一直殚精竭虑地向他隐瞒着。他们做得十分成功,堪称奇迹。这种恐怖可怕的沉默令他抓不到一点蛛丝马迹,可以使他明晓这些奇怪的机关。
在《对话录》中,沉默充斥着所有的角落,心与心之间有无限长的距离。我们猜不透卢梭的谜团,就像那些穿不透的墙,挣不出的网,走不出的迷宫,跳不出的陷阱,一切都意味着不可穿透和老谋深算。
阅读《对话录》的气氛,就如同当年读卡夫卡的《审判》,主人公在庭上接受审判,而法官却隐了身,这使得整个局面看起来就像一个巨大的谜团,引诱着我们走进去,而后,深陷其中。
对后世读者而言,《对话录》不仅是一部极具文学价值的对话体杰作,也是一册记述卢梭生平的微型自传,更是一把理解卢梭思想的钥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