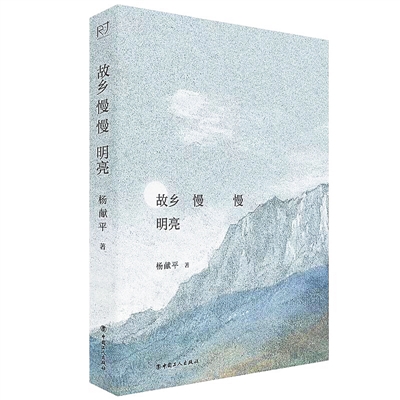■ 贺颖
在新近出版的散文集《故乡慢慢明亮》一书当中,作家杨献平如是说,“尽管我走了很远,身体在他处停留,内心精神和骨血仍还在原地”。对于别离故乡多年,在时间中,不断被其他地域及其文化磨炼的人,对于故乡的觉悟,杨献平是猛然的,也是深刻的。世事如此繁复,人在其中,不断变化,心境、趣味和思想,被迫流转或者自觉发现,都是一个必然而又可贵的过程。
因此,当一个人的精神转向故乡的方向,记忆就成了奇异奇幻的放大镜,开启的是全景式的视野;亦是最精细的显微镜,故乡的躯体里,那些阴暗幽微的细小汗毛和血管,无一不纤毫毕现。其中既有对自然存在及其显著之物的描写,又有形而上的体悟与发现。如杨献平对荆芥、柴胡、黄芪等草药及犵羚(松鼠)、野猪、秃羯(猫头鹰)、知了、蝎子等动植物的精神赋予,以及四季农事的描绘,都体现出了诗意性和浓郁的农耕色彩,在今天看来,一切都那么遵循自然本性,又具备了诗意与审美趣味。
杨献平对故乡南太行乡村的文学书写,不只是山川草木等地方物候和风物,还有具体的人物及其故事,尤其是他们的命运遭际与现实困境,正如杨献平所言:“只有人,才是村庄的生命力所在。”
多年前,离开故乡南太行的杨献平,是义无反顾的,他甚至发誓,一生都不想再回来。可事实上,我们每个人无论走多远,生命、心灵和精神的最终归结点,还是出生的地方。在某一时刻,中年的杨献平在城市的灯火之中,豁然顿悟,开始与故乡和解。
此去经年,黑发渐生花白,从华北南太行到西北的巴丹吉林沙漠,再从瀚海戈壁容身成都,杨献平始终与故乡发生着深度关联,一种是内心的和现实的,一种是精神的和文化的。他不断地书写自己出生的那一片地域,试图建立起自己的一块文学地理。在《故乡慢慢明亮》一书中,杨献平笔下呈现的那些“繁茂众生”,如星辰朗月,高标出众,他们构成了南太行乡村最核心的文学风景,当然也从中体现了世道人心和复杂多变的人性幽微。
对人性之中善与恶、清朗与混沌,杨献平经由直面与探究,叹息与怀念,直至于精神最深处,结晶出向死而生的彻骨空寂与悲悯理解,这一切也正是文学文本永恒的魂之所在。可以说,杨献平笔下正在生成的是留给未来的“历史”,杨献平说,“在村庄的所有人,不断生长、青壮和老去,一个被另一个替代,深长的血缘就像天书,一笔一画都是平民历史”。南太行的乡亲们,因为杨献平的书写,不再仅仅是草木一秋的刹那,白驹过隙的倏忽,那些曾经存在过的人们,必将于一册文本中接近不朽,这也许是文学最深沉的慈悲。正如杨献平所说,“村庄、他们、我,在的和不在的,新生的和老掉的——他们都是我的,我也是他们的。”
《故乡慢慢明亮》是一次全景式的回望,是一颗心经年瞻前顾后又反复下定决心、时常咬牙切齿又一再出尔反尔之后的一次灵魂长旅。少年时毅然决然地出走他乡,而中年后,却终于于某一刻宿命般倏然驻足,无端侧耳,聆听遥远天地间那一缕芜杂的乡音。脚步忽踉跄,眼角湿润。如此方才惊觉,自己与故乡的精神脐带从不曾剪断,故乡的一切,于自己的精神旅途中从不曾消逝分毫。无眠的子夜,当异乡的声色犬马复归安静,故乡曾经黯淡的灯盏悄然渐次燃起,故乡,那古旧而确切之面目自此渐渐明亮。
这是一个作家眼中心里关于南太行的时间简史,南太行,因为一个个体于流年喧嚣中执着于精神明亮的文学书写,有了自己独属一方的时间履历,这是南太行的骄傲,更是一脉宗祖面对自己后续子孙一般的浩大慰藉。这简史又极丰盛,因为里面有一个村庄确凿而漫长的碑文。
《故乡慢慢明亮》亦是一个作家的个人心灵年表。每个远走他乡的写作者,也许都有一个自己心中的“故乡南太行”,那里同样有魂牵梦萦,亦饱浸五味杂陈,但并不是每个人都有意愿与能力,将自己的故乡于岁月的时空中全景式呈现。正是杨献平巨大的心灵愿力,才成就了这一册“学术的故乡”“文学的故乡”“美学的故乡”,乃至“慢慢明亮的故乡”。
有时美学的最高策略也许就是没有策略,当南太行的山风千百年如一日地拂过那片山野大地,当那些在的和不在了的人们在心底纷纷醒来,当岁月狂奔的列车渐渐放缓了脚步,文本的诞生就是水到渠成的流淌,也仿佛揭开某个永不愈合的伤口,血永远鲜活奔涌。文字如血如水从作者的心中,从屋顶的星群之间,从父母及邻人的炊烟里,从亲人安息的墓野,从一个人、一群人的命运深处汩汩而来,汪洋恣肆,无遮无拦。
这是文本的幸运,亦是文学的可遇不可求,仿佛山河大地天然沉积酝酿而成的宝石,无须打磨便流光溢彩。这样的光彩,应是来自一个人基因里的诗人属性,一直认定诗人的杨献平,比散文家的杨献平更具力量,恰因如此,这一卷浑然天成、悠长繁复的时间简史与心灵年表,字里行间,无处不萦溢着自内而外的诗性光亮,陡然具有了文学的美学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