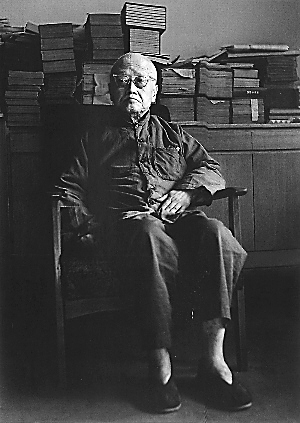民国时期,俞平伯和周汝昌是胡适的两大弟子,但是,他们两人在发挥老师胡适在《红楼梦》研究的观点上的研究方法是不同的,俞平伯是向内的,他是从《红楼梦》文本之内找证据,属于所谓的《红楼梦》的“文评派”,而周汝昌是向外的,也就是到《红楼梦》文本之外的曹雪芹的家世中找证据,属于所谓的《红楼梦》的“考证派”。《红楼梦》的“文评派”的研究成绩的大小取决于研究者的鉴赏分析水平,《红楼梦》的“考证派”的研究成绩的大小取决于研究者对于材料证据的新发现。俞平伯以自己卓越的鉴赏分析水平勤奋研究《红楼梦》,写出了《红楼梦辨》等学术著作,《红楼梦辨》与胡适的《红楼梦考证》一起被公认为是新红学的开山之作。
早年,俞平伯在《红楼梦》的研究上曾有两大心愿,一个心愿是办一个研究《红楼梦》的专门刊物,另一个心愿是把许多《红楼梦》的版本聚在一起,进行《红楼梦》版本的校勘。俞平伯的第一个愿望未能实现,但是,他的第二个愿望在后来完成了。
俞平伯在研究《红楼梦》时,他看到《红楼梦》第一回开宗明义给读者一连讲述了两个神话故事:一个是顽石补天无望、下凡历劫的神话,一个是神瑛侍者施惠、绛珠草还泪的神话。俞平伯就对此质疑道:“两个故事平行,交而不叉。绛珠自以眼泪还侍者甘露之惠耳,与顽石又何干?”
那个特殊的年代,俞平伯所收藏的有关《红楼梦》的书籍,都被以“四旧”之名而被抄收殆尽,其中就包括1960年台湾出版的影印朱墨两色的写本《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后来,俞平伯的被抄书籍清退归还时,俞平伯发现他的《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一书上却盖上了康生的大印,俞平伯感慨道:“我的‘宝贝’(指《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一书)被抄后就变成了康生的‘宝贝’。”
俞平伯对于在《红楼梦》上很有研究的顾颉刚很佩服,他写有《追怀顾颉刚先生五绝句》的诗:“昔年共论红楼梦,南北鳞鸿互倡酬。今日还叫成故事,零星残墨荷甄留。”在这首诗的后面,俞平伯还写了跋:“1921年与兄(顾颉刚)商谈《石头记》,后编入《红楼梦辨》,乃吾二人共学之成绩,当时函札往还频多,舍间于今一字俱无,兄处独存其稿。闻《红楼梦学刊》将甄录之,亦鸿雪缘也。”记述了他和顾颉刚在研究《红楼梦》中的真挚友谊,以及他对顾颉刚的感佩之情。
二十世纪中期的一个暮春三月,和俞平伯在同一个干校里下放劳动的吴世昌,在水塘边洗涮时,见到水塘里菱叶新发,回来后他兴冲冲地对俞平伯说:“我仔细看过了,菱是不开花的。没有花,哪来香?金桂把香菱改秋菱,有道理!宝钗的学问也有限。夏家小姐并非不通文墨!”俞平伯是苏州城里人,他不未曾留意过菱花之有无,竟然一时语塞,不知如何回答。这时,在场的钱碧湘关于菱也开花的解说为俞平伯解了围,那天中午,在去食堂的路上,钱锺书笑着对钱碧湘小声道:“碧湘,你今天帮俞先生(俞平伯)打了一个大胜仗!”见钱碧湘不解,钱锺书又说道:“吴先生(吴世昌)和俞先生(俞平伯)是学术上的冤家呀!”众人大笑。
1980年,俞平伯在给周颖南的信中写道:“《红楼梦》成为‘红学’,说者纷纷,目迷五色。我旧学抛荒,新知缺少,自不能多谈,只觉得宜作文艺、小说观,若历史、政治等尚在其次,此意亦未向他人谈也。”表达了他对于《红楼梦》的研究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