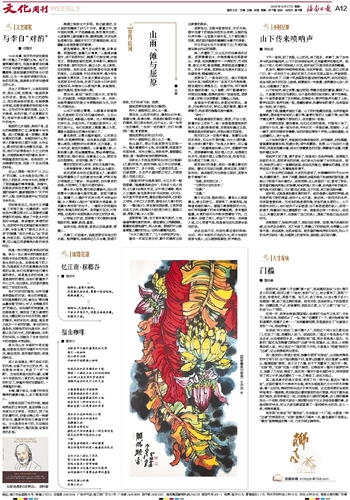■ 符志成
下午一场雨,到了夜里,山上的风,凉了很多。夜静了,除了虫鸣声与机房的嗡鸣声,山下不时传来唢呐声,还有敲锣声和钹击声。那是山下有人在举行送别亲人仪式,或许他们只是在寻求某种慰藉。
机房外,樟树叶哗啦哗啦地响,在低声絮语。此刻,我伫立机房门口,夜一点点沉下去,起初还有几只虫豸在草丛里叫,声音细弱。后来虫鸣也淡了,只剩下机房里服务器运转的嗡鸣声,低沉而恒定。我坐在机房外的石阶上抽烟,烟雾被风一吹就散,连带着杂七杂八的念头,也跟着淡了些许。
山下唢呐声,穿过夜雾,越过树冠,带着点涩涩的颤音,飘到了山上。不是喜庆的《百鸟朝凤》,也不是热闹的《抬花轿》,调子沉得很,每一个音符都像浸了水的棉线,拉得很长,锣声和钹声也跟了上来,锣声闷闷的,钹声则脆一些,透着股凄凉,和着唢呐的调子,在夜里织成一张网,密不透风。
我掐了烟,循着声音往下望。山下的村落藏在夜里,乐声却越来越清晰,想来是吹唢呐的人歇不得,敲锣打钹的人也歇不得,他们得守着这调子,陪着那个要走的人,走完最后一段路。
小时候在老家,看戏看斋,也见过这样的场面。村里有人走了,总要有个仪式,请一班乐手来,吹吹打打一夜做法事,送魂呢!人这一辈子,来的时候安安静静,走的时候总得有个声响,让魂知道路,也让活着的人,有个念想。
山下传来的调子,声音被风吹得有些变形,时而清晰,时而模糊,像隔着玻璃看东西,轮廓分明,细节却朦胧。我想,山下此刻灯火通明吧,灵堂前挂着白幡,亲友们穿着素色的衣服,围着棺木坐着,沉默地听着这乐声。
唢呐声又变了调,调子更低了,那是有人在低声呜咽。我想起几年前的冬天,老同学走的时候,他们家也为他请了乐手和法师。那天,唢呐声从街口一直飘到家里,我站在灵堂边,看着他的遗像,还有哭成泪人的妻儿,听着就是那调子。
山下的乐声还在继续,午夜的风更凉了,吹得樟树的叶子沙沙作响,和着那调子。我伸了伸腰,想起机房里那些不知疲倦的服务器,想起山下那些不知冷暖的人,忽然觉得,这山夜里的一切,都有了联系。服务器的嗡鸣声是山的脉搏,唢呐声是人的心事,虫鸣是中秋的温存,弯月是天空的窗口,它们都在这夜里,互不打扰,却又彼此陪伴着。
或许吧,这就是离别最本真的样子。或许是撕心裂肺的哭喊,或许是肝肠寸断的挽留,或许什么也不是。就这样,一段沉沉的乐声,在夜里慢慢流淌。它送走的是逝者的魂,安放的是生者的心。山下那些吹乐的人,他们或许不认识逝者,也不熟悉逝者的家人,却用一段调子,陪着他们走过最难熬的一夜。就像我这样一个陌生人,站在山上,听着这段调子,也想起了自己的亲人,想起了那些已经远去的时光。
夜渐渐深了,唢呐声也弱了,却依旧没有停。我想,等天快亮的时候,这乐声总会停的。风又吹来了,带着山下的唢呐声,也带着山上的草木香。我站起身,往机房里走。服务器的嗡鸣声依旧低沉,和山下的乐声交织在一起,如银屏上的信号柱、音柱般,忽闪忽闪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