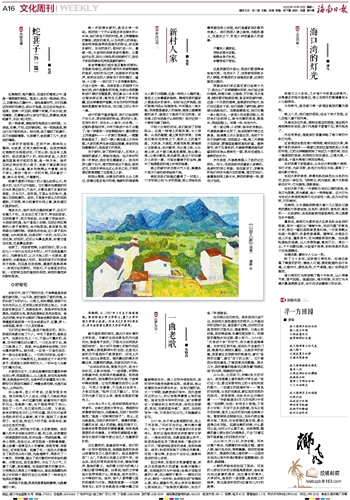■ 李静润
李静润,女,1997年4月生于海南琼海。陕西师范大学文学学士,澳门大学中国文学硕士在读。作品见《万泉河》等杂志,多次在校园主题征文活动中获奖。
窗外是热闹的街市,屋内只有冷清的文字和我。平静的生活在黑色的月光里沉沦,就像海子说的,“万里无云如同我永恒的悲伤”。年少时只有满心的锐气和狂傲,能得以拥抱期待中的生活,这是在从前的日子里我所不敢想象的。好在上天怜悯,总归尘埃落定。随风飘远的潮水苏醒过来,在朦胧的拂晓,在昏沉沉的午后。
“去年此时此地,黄昏天边外,我与少年初见,云影共徘徊。”一曲老歌,伊萨科夫斯基作词,杜那耶夫斯基谱曲。我流浪的、漂泊的,我浅薄而无知的灵魂,于旋律中得到救赎。过往的晨曦在我的心头掠过。只觉人生寥寥,不过是归去来兮。大抵应如是,“轻舟已过万重山”。可往日的光影又回过头来,滴落在眼前的窗台上。
2016年8月8日,我来到陕西师范大学读书。主修汉语言文学专业。想起那句罗曼蒂克的独白,冯雪峰说,见到丁玲时的感觉,“就是一见钟情的样子”。那么,这也就是我,见到大学的样子。清晨的树影、日暮的水面、迷人的老路、斑驳的巷子口,依稀传来零零碎碎的朝朝暮暮,传来晃晃荡荡的点点滴滴。文学院的课程很丰富,我在忙碌的日程中度过自己人生重要的阶段。
记忆最深的,是基础写作课。我们的第一位写作老师姓梁,她眼里温柔的秋波让我看到自己心里的春天。她总是称呼我“丫头”,于是我从此爱上这两个字。毕业后,我还时常同梁老师交谈,聊她的歌声、聊她的散文。她的散文《时光的情人》《遇见》都写得很美。如果说,她的文字曾经为我带来些什么,那就是,我失恋的心从中得到疗治。或许,每个人都带着心里的伤痛努力行走。想起那首歌——《如果有来生》,似乎生命就是在半睡半醒之间重新得到生长。第二位写作老师姓刘,我的写作风格受她影响至深。或者说,她让我看到生命的原生状态。没有记错的话,大一下学期,她教授我们写作。因为是黄河边的女儿,所以性格带着黄土地的坚韧。她谈生活与写作的关系,说“你需要这一切铸成你文学的肉身,走向自我毁损,然后,在破碎里吟唱”。是的,生活和写作一样,只有我们忘记它,才能重新认识它。
2017年,处于学业瓶颈期的我,迷上了苏东坡。“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我一口气读完了林语堂的《苏东坡传》。其时正逢柏老师在讲授唐宋文学史。一度低迷的我,在教室里垂头丧气。柏老师给我私发了微信消息:“最近你状态不对。”阅读完柏老师的消息,我泪流满面。或许,柏老师早就不记得这件事情,可我一直记得,永远也不会忘记,感激柏老师的用心良苦。
回过神来,发现苏东坡屡遭贬谪,却成为自然里伟大的顽童:他偶尔喝得小醉,在倾城的月光中徘徊;他偶尔写些可爱的小诗,在山楂树下散步……哪怕仍旧失去,哪怕一无所有,他却把生活“写得那么美,那么遒健朴茂,那么字字自真纯的心肺间流出。”“他保持天真纯朴,终生不渝。”林语堂说。
往日烟云往日流花。其实我早已说不出,收到师大录取通知书的那天,心中是如何的百转千回,甚至都不记得,当时的天空是怎样的万里无云、澄澈清明。只是从那时起,我变得坚强、执着而更加努力。校园里的植物亦如这般,微小有力。2018年,“天凉好个秋”的时节,师大愈发显得厚重。长安校区图书馆,面向孔子圣像的门庭,格桑花从南到北蔓延。比起芬芳的玫瑰,我更爱这自然野性的格桑花,爱它“坚持的位置”,爱它“足下的土地”。它不曾因冷雨而褪色,不曾因寒风而萎靡。弱水三千,我所看重的格桑花正焕发着“西部红烛”的光明,洒满我的世界。
2019年,大四实习,讲解《秋天的怀念》。老师借着上课的契机对学生说:“我们这一生,都应该要有向上的斗志和向前的毅力。一如课文的结尾所写——‘黄色的花淡雅,白色的花高洁,紫红色的花热烈而深沉。泼泼洒洒,在秋风中正开得烂漫’……”作家路遥在《平凡的世界》中写道:“生活啊,生活!你有多少苦难,又有多少甘甜!天空不会永远阴暗,当乌云退尽的时候,蓝天上灿烂的阳光就会照亮大地。青草照样会鲜绿无比,花朵仍然会蓬勃开放。”其实,无论苦难还是甘甜,都会显得云淡风轻。回望往事的时候,什么都可以说,也可以什么都不说。后来想想,稚嫩的童心要比我们开阔得多,不会“只看见院子里高墙上的四角的天空”。
2020年11月23日,长安初雪。风吹过整个海岛,在踯躅的华年里交错。望向人群,皆行色匆匆、熙熙攘攘。那时的我潸然泪下。想起昨天晚上做的梦——三朋四友站在山地中欢唱《青春友谊圆舞曲》,拉起手、跳起舞。
人群的声音将我拉回了现实。可我的心却在平淡的云烟里晃荡起来,恰似星光划过寂静的黑夜、划过漫长的寒冬。大学时光,是我的一曲老歌,是我海上的挂牵。那正是我听到的《红莓花儿开》的旋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