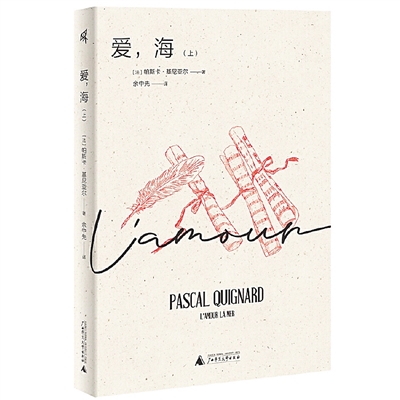■ 海南日报记者 杨道
“每个港口都朝着汪洋大海,仿佛紧紧地抓着无限。”《爱,海》是法国当代作家帕斯卡·基尼亚尔的最新长篇小说。基尼亚尔是法国至今在世的最伟大的作家之一,他对哲学、历史、艺术均有深入的研究,这使得他的作品带着一种别处的文明的奇异魅力。他的创作风格类似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勒克莱齐奥,朝向历史与社会的边缘。
《爱,海》是一部并不十分贴合小说特质的小说。小说写的是两位乐器演奏家的爱情故事,在交织着鲜血与泪水的17世纪,在彩虹消失的海边,激荡着这两位演奏家弹奏的不朽旋律。
《爱,海》是一部长篇小说,是基尼亚尔作品中较厚的一部。但很明显,该书的内容闲散凌乱,内在的彼此呼应需要一个漫长的距离。事实上,这个距离正是这篇小说的迷人之处。小说的女主人公图琳是一位演奏者,同时也是一位在航海中失踪的船长的女儿。于她而言,大海就是“彩虹诞生的地方,太阳永不落下的地方,夜晚只在蓝色的暮色中结束的地方”。她总爱穿“蓝灰色的绸缎面裙袍”。作者的这种描述让小说充满画面感,海不再显得那么空而单调,它充满灵动的色彩。
图琳一年四季都喜欢在大海中游泳,裸着身体。这一点,似乎以暗示的方式应和了小说的标题“爱,海”。某种意义上,标题中的这两个字,也隐含着女主人公的性格特征。而与之相对的,是极富个性的男主人公哈腾,他“曾梦想成为一个教士”,但他从青年时代起就在整个欧洲游荡。他是著名的鲁特琴演奏者,也是著名的乐谱抄写人。他们在1650年代相爱了。他们的相爱,使得音乐作为主题突显了出来。
在基尼亚尔的作品中,音乐就像是一种执念,一个梦魇,一条通往他的文字世界的神秘金线,他小说中的主要人物几乎都是音乐家,或者乐器演奏者。或者他意识到了自个小说的“散”,因而,他习惯性地在小说里设一个日期坐标,譬如《爱,海》中的1650年代。他通过这个日期,把音乐、绘画、爱情与死亡串联起来,然后放置于历史坐标中。
阅读《爱,海》的过程,可以滋生很多新鲜的感受。它不是一种传统的小说形式,而是叙事与思辨的杂糅,作者早前的很多作品都采用了如此写法。小说中融入了作者对艺术、历史、哲学的思考,溯源音乐在生命原初对人格的塑造,回顾音乐在生命的尽头给人带来的感动。
作者细腻的文笔是我喜欢这部小说的原因之一,箴言式的语句悠扬婉转又顿挫有力。此前读他的另一部作品《音乐课》时,就对其中一些场景描述颇为触动:
马兰·马莱在偷听,挨着一道隔障、一块发声的地板——已是一把乐器的一间小木屋。耳朵贴着树,身体下蹲,这位偷盗的音乐主角在重现一种更为古老的姿势。那场景曾是妊娠,后来成了分娩。
而在《爱,海》中,他仅用了三行文字,就把海潮的神秘与辽远展示出来了:
海潮越大,离死亡越近,那海滩就越壮丽。
奇迹就越不连续,就越广阔。
世界越深,黑夜就越巨大。
他的文字读起来极富韵律感。这使我想起他创作于1991年的小说《世间的每一个清晨》,后来改编成了经典电影《日出时让悲伤终结》。这是一部用一帧帧古画铺砌而成的法兰西文化画卷,静谧、古朴,如诗如歌,缓慢平静的长镜头将悲伤隐藏在静静的叙事里,弓弦的碰撞却表现了人物心中的波澜,翻滚着呼啸不停的记忆。
《爱,海》的层次感似乎更甚于《世间的每一个清晨》,或许它将来亦能成就另一部经典电影,以彩虹和音乐来描摹“最美的女性肖像画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