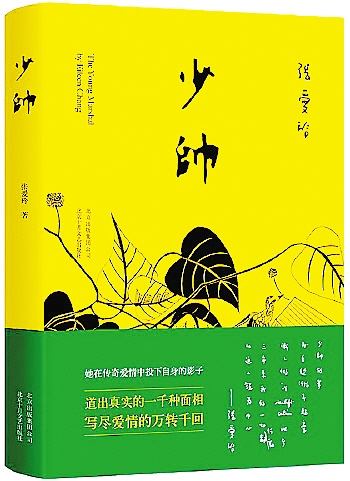张爱玲的佚文遗作的发掘,就像前苏联的一位“撑杆跳高”运动员,——在奥运会和世锦赛上,每次都将自己保持的记录提高1厘米,一直保持了十余年。张爱玲的全集前些年早就出了,连以搜集现代文学史料闻名、雅称“张爱玲的未亡人”的陈子善教授,也开始在张爱玲编剧的电影上听录台词,从上海小报上找到的佚文,宋家所藏的张爱玲遗稿,还有分散在各处的张爱玲书信,又开始一轮轮、一年年的“轰炸”,几乎每本都会引起或大或小的话题或“热潮”。为什么呢?只有一个理由,因为张爱玲呀!
这本新近出版的《少帅》也是如此。一位朋友迅疾在网站上买了一本,“因为是张爱玲呀。即使是别人翻译的。”前些天,宋以朗、陈子善在北京大学百年讲堂开这本书的首发式,一位喜欢朱天文的同学参加了首发式,又读了书,疑惑兼感叹跟我说:“你读了《少帅》么?这就是借一个历史框架写流苏和九莉呀”,“这是一个张爱玲的平行世界”。
历史与小说的艺术
据《少帅》所附的《别册》介绍,这部张爱玲所写的英文历史小说,构思于1956年,写于1963年左右,但只完成了三分之二,就搁笔。此后,张爱玲对“张学良”这一题材失去兴趣,最后未完成。张爱玲去世后,宋家将遗稿复印本赠送给一家美国大学,从此石沉大海。直至近年,宋以朗决定找翻译,和这几年相继出版的张爱玲英文小说《雷峰塔》《易经》《小团圆》一般,最终得以面世。
在这些时间节点上,最关键的当然是1956年至1963年,彼时张爱玲正在美国,这位最知名的华文小说家,意图用小说打开美国的大门,而获得安身之地。1963年正是张爱玲的“幸运年”,张爱玲正在写《少帅》。《少帅》写的是张学良和赵四小姐的故事。在民国初年,从北洋军阀时代的张作霖,到西安事变的张学良,这位被称作是“少帅”的张学良显然是中国“系天下安危于一身”的人物,而后又被终身拘禁,又构成这位“少帅”的奇特命运。张爱玲此时决定来写《少帅》,也许既有出自题材的考虑(“中国符号”),更有她一贯在历史中寻找个人命运的写作趣向,正如《倾城之恋》里,一座城的陷落成全了一对男女的爱情。或者说,一座城的陷落只是为了成全一对男女的爱情。而在《少帅》里,有张学良和赵四小姐,赵四小姐说过的一句话,触动了张爱玲的心弦:张学良的拘禁,反而成全了赵四小姐。因张学良,这位合书生、军人与花花公子于一身的新军阀,当他处于被拘禁的境地时,反而能与终身追随他的赵四小姐相依为命。这桩关系到一个国家、比一座城市陷落更大的历史事件,最终竟然成全了一对人儿。
《少帅》写民国初年,从张作霖进入北平到张作霖被炸死,再到“东北易帜”、张学良去南京就职。这一段历史风起云涌、纷纷芸芸,用鲁迅的诗就是“城头变幻大王旗”,但尽销于小儿女的喃喃话语之间。为了写这一段历史,张爱玲曾经想去台湾实地考察,也曾翻阅港台杂志的忆旧文章和传记,果不其然,在小说的一些细节里,研究者找到了彼时杂志上的文章的改写,但更多的是无从查考。除非是能找到张爱玲当时的阅读书单,就像最近有人从国家图书馆里找到王国维当年阅读的西文书一般。比如以下这一段写看戏:
她见过中途有些人离开包厢,被引到台上坐在为他们而设的一排椅子上。他们是携家眷姨太太看戏的显贵。大家批评这是粗俗的摆阔,她倒羡慕这些人能够上台入戏;尽管从演员背后并不见得能看到更多。
这种观众上台看戏的习俗,已是多年不见于舞台。这些年来,也只见过昆剧《1699桃花扇》里,在大舞台上摆上椅子,让没有表演的演员坐着当看客,观看小舞台上的表演。但这种场景,倒可以当做张爱玲对于世间的一种观察和隐喻。也是小说中的作为小女孩的“周四小姐”(赵四小姐在《少帅》中的名字)的一种人生感想。
然而,通过材料重写历史细节之外,更重要的是小说的视角,那些情感的细节,倾注的却是张爱玲的自己。正如张爱玲所说:“历史如果过于注重艺术上的完整性,便成为小说了。”在《少帅》里,虽然经过翻译的“流失”,但那种张爱玲气息,仍然扑面而来。比如写“周四小姐”想了解“少帅”,想了解成人世界的愿望:
她是棵树,一直向着一个亮灯的窗户长高,终于够得到窥视窗内。
而“周四小姐”和“少帅”之间的感情和往来,既像《倾城之恋》里的白流苏和范柳原,又像《小团圆》里的邵之雍和盛九莉,也即,是一种张爱玲特有的情感经验与模式。张爱玲在书写张学良与赵四小姐的故事的过程中,逐渐偏离和改写了历史中的人物,而把他们变成自己的故事中的一个个化身。
张爱玲与胡兰成
张爱玲与胡兰成,这一对民国文坛的著名文人情侣,他们的故事,经由胡兰成的《今生今世》里的《民国女子》,已为大众耳熟能详。诸多细节与金句,都已成为当代习语与野史的一部分。胡兰成在日本将《今生今世》寄给美国的张爱玲,但并无回应,似乎是这段故事的结局。然而,近年来出版的《雷峰塔》、《易经》、《小团圆》、《异乡记》、《少帅》等张爱玲遗稿,极大的改写了这一故事。因这几部作品,《雷峰塔》、《易经》、《少帅》皆有胡兰成的影子,《小团圆》是二人关系的隐写,《异乡记》是张爱玲用中文写的寻找隐遁在温州的胡兰成的一路旅程。由此可见,张爱玲不仅是为胡兰成开启写作之秘密的天启式的人物,胡兰成亦是张爱玲纠缠不清的一个主题。或者说,在张爱玲的文学经验中,胡兰成是一个刻骨铭心,以致被反复书写的一类角色。
在《少帅》里,“少帅”与“周四小姐”的情感故事,是不是另一个平行世界里的“胡兰成与张爱玲”呢?有人指出,这或许与纳博科夫其时正在美国流行的《洛丽塔》有关,《洛丽塔》不就是写一位中年男子对一位“小萝莉”的不伦之恋么?“少帅”与“周四小姐”恰好亦如此。但如考察胡兰成与张爱玲彼时的年龄,也与这种年龄的相差相合。更重要的是,在《少帅》里,“周四小姐”对“少帅”的那种倾慕,一个小女孩眼中的情人的光辉,和张爱玲的表达何其相似,譬如这一金句:“见了他,她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但她心里是欢喜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这是在《今生今世》里,张爱玲送给胡兰成的照片后所题的字。这种全身心的卑微的喜悦,不正是洋溢在小说《少帅》的整体氛围里么?而几经波折,在餐桌和客厅里,太太小姐们所谈论的民国风云过后,“少帅”与“周四小姐”因缘聚合,成其好事之时,那句“岁月静好,现世安稳”又何其能反映“周四小姐”此刻之心意。
在《少帅》的结尾,张爱玲写到:“下一次南行,太太们也与他同坐一架私家飞机。终于是二十世纪了,迟到三十年而他还带着两个太太,但是他进来了。中国进来了。”“少帅”与“周四小姐”的故事到此戛然而此。据张爱玲原初的构思,这只是小说的三分之二,之后必定还会有“西安事变”,这才是决定小说中“少帅”与“周四小姐”之终身的“倾国之恋”。或许,还有在台湾的幽居等等。但是张爱玲已经厌弃“张学良”这个角色了,这有点像她后来再也不回应胡兰成一般。小说《少帅》或许没有写完,但张爱玲心目中的“少帅”已经写完了。
“平行世界里的张爱玲”,依旧是张爱玲。那朵花在尘埃里开放,经历世事后,又枯萎了。在一个个由张爱玲的文字构筑的世界里,来来往往的人与世,依然是张爱玲,依然是花开花落,人世轮转又无常。